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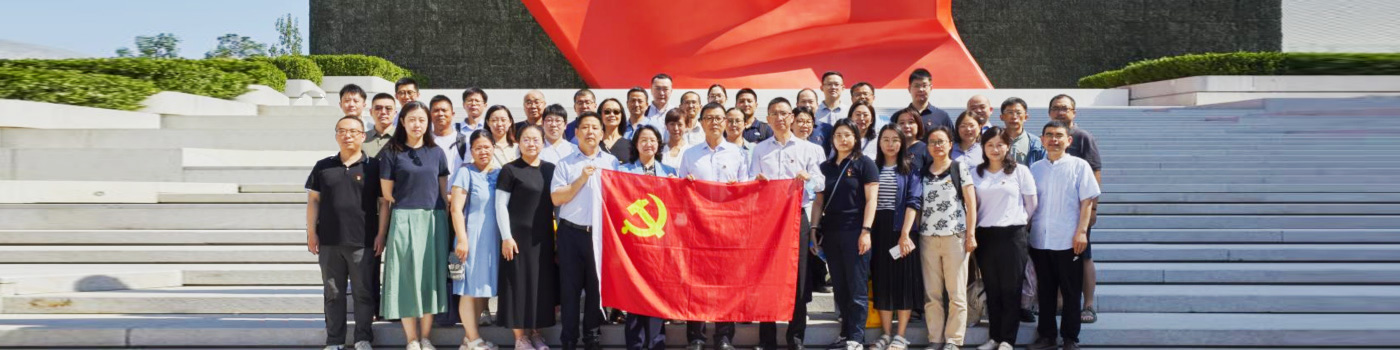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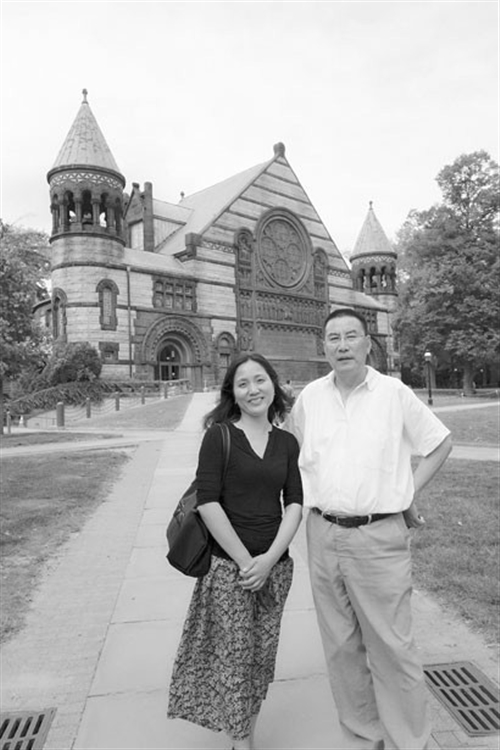
本文作者(左)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吴以义教授
●人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在中国读者群中,这还是个未被充分注意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追问,会给我们带来认识论、哲学、历史和宗教等诸多领域的深刻教益。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坚信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而这种认识表现在基于理性的理解。在历史上,理性的即斯宾诺莎的上帝与世俗的即基督的上帝互为表里。
中国向西方的学习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从1842年魏源所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之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着眼于西方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而不是“态度和精神”。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在实际上忽略了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自我认识和心灵探索的巨大启蒙作用。吴以义教授的新作《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梳理从哥白尼到牛顿近两百年间日心学说的发展史,以经典个案的方式讨论了科学、宗教与理性的相互关系。信仰的理据与阐释是题中应有之意,更是这一历史要案的恢弘背景。从事语言民俗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李明洁就此赴普林斯顿大学采访了该书作者、科学史专家吴以义教授。
吴以义教授系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师从C.Gillispie和N.Sivin教授,研究西洋和中国科学史;曾任纽约市立大学兼任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科学研究基于对理性的坚定信念
李明洁:您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国人只是引进了“科学做了什么”的结论,却没有理解“科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吴以义:时光倒推一千年,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如果你认为历史是理性的,那么,你要给我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认为研究“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古人当然要研究科学,科学当然是要研究的。其实古人的想法和我们现在的想法很不相同。古人生病了,并不研究是不是吃了脏东西,而是认为他们需要去祷告。在这个问题上追问下去,研究科学或者说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必然要有一个为当时社会所能理解的动力。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常常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其实研究科学本身有没有意义,并不是自明的。司马光就明确说过:研究天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治理国家——皇帝圣明,大臣称职,儒学贯彻,这是保证我们幸福的基本源泉。天上的事情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虚费人工”。
李明洁:可见东西方对于科学的功用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西方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呢?
吴以义: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宇宙万物是上帝向人提供的一个途径,理解自然就是理解上帝,因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把他的智慧放在了自然,让人由此去发现他的智慧本身。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竟然这么井然有序,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它是完全盲目地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一个智慧的上帝创造的呢?
李明洁:那么,现在我们仍旧认为这个上帝真的是指向一个具体的人格神,比如耶稣?或者说,科学家在做最初的研究的时候,的确是指向一位人格神的吗?还是指向人所不能理解的某种超级的能力?
吴以义:都不是的,是指向了爱因斯坦说的,斯宾诺莎的上帝,即理性的上帝。就是坚信“自然界是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这两句话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这两句话得不到保证,科学研究就没有了意义。我确定我的研究是会有结果的,我可能犯错误,但是我要研究,我要找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李明洁: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就是在接近斯宾诺莎的上帝。斯宾诺莎认为,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和上帝就是一回事,这个上帝包括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通过理解这种深层的逻辑关系而产生的宗教感觉,实际上是面对物质宇宙所展现的规划而感到的敬畏感。这不同于那种人们平常所说的宗教感觉。那么这个理性的上帝和世俗宗教里人们信仰的那个上帝是什么关系呢?
吴以义:互为表里。上帝的根本属性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同时上帝的神性又表现在他的不可理解性。上帝让我们理解多少,我们就理解多少。这是个最纯粹的基督教说法,也是往往被大家忽视的。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彻底的逻辑分析的话,会发现这里有些不自洽:一方面我们在强调理解上帝,另一方面上帝又是不可理解的。那么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呢?我们只能说,上帝创造世界,把规律放在这个世界当中,目的就在于对人的智性的启示,使得人通过认识这种规律来认识到上帝创造的伟大。
宗教信仰与科学信念是相通的确信
吴以义:上帝创造世界的启示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话语,God’sword,具体就是《圣经》。但是语言本身存在一个理解问题,上帝讲的话你听不懂,怎么办?所以,另外还有一条就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所谓God’swork,bookofwork。到科学革命高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尖锐地提出来,《圣经》有些东西和自然所揭示的规律不一致。有人就认为是不是《圣经》错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一般认为不是这样的。《圣经》是语言的,简化的,必须用你可以理解的形式向你传达。如果上帝那个时候就对你说很复杂的科学的内容,你听不懂。比如,《圣经》说上帝用泥土造人,是不是真的是地上抓一把土来造人呢?不一定是,这是一个比喻——上帝用了最普通的,但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造人。这是宽泛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把《圣经》逐字逐句地解释,并不符合上帝原来的意思。基督教有些派别认为这是一个启示,它只是给你一个启示,上帝并不打算教授科学。
李明洁: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说,《圣经》用话语阐释的神的意志和规律是讲给普通民众听的;另外一种是讲给天才、讲给接近上帝的人也就是科学家或者是智者来听的呢?
吴以义:不是。因为一般的老百姓也在感受自然。你抬头看天,太阳为什么这样有规律地升起,一年四季为什么这么有规律地更替?没有一年四季就没有了农业。你想一想,就会相信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这一定是有计划的创造。不识字的人也能够理解上帝。
李明洁:可见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科学研究的宗旨,都会归向对宇宙神秘力量的确信(我们姑且笼统地称之为“上帝”),并支持这样的确信。这样的信念恐怕已经为理性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理性。这样的上帝或者说这样的理性,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中可以有不同的名称,老百姓所谓的“天理”,《老子》所言之“道”,也与斯宾诺莎的上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然而,这种确信对无神论者来讲,矛盾会非常剧烈。
吴以义:无神论如果贯彻到底,就遭遇到“最后因”的问题。对无神论者而言,最尖锐的问题是你怎么证明甚至最低限度地说明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有规律的?你认为世界是规律的,你为什么这么认为?规律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说这个规律是存在的呢?这是一种信仰,或者叫做信念。哪怕是最最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客观世界还是需要一个信念,包括两个方面,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存在的,这个规律是能被人认识的。
李明洁:这样说来,通常我们含糊地称作信仰的东西和科学研究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宗教和科学是矛盾的呢?
吴以义: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基督教的有些教派要坚持《圣经》的“章句解”,就是字面解释。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涉及对当时的天主教教会的挑战。他们不是仅仅讨论你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而是在讨论你有没有资格解释《圣经》。我们常常会把这两个问题混淆,因为教会的反对主要不是因为你解释错了,而是你怎么把我这个独一无二的权力给拿走了。
李明洁:了解了宗教和科学的相关性之后,我们由此再来看康德的名言,可能就会发现其中的理据性。他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星空和道德,科学与宗教,都引导人类不得不去思考“上帝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康德惊奇并敬畏的实际上就是科学与宗教中的“上帝”。当然,康德批判哲学中的上帝只是个“理性”理念,其功用只是给予有条件的现象以无条件的调节与范导。康德非常明确地指出,为了便于理解或者思维“上帝”的需要,当我们明白了他只是个范导的理念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赋予上帝这一道德理念以传统神学的所有特征,如全智、全能、全在等等人格属性。
科学革命分化了科学和宗教
李明洁:科学研究和宗教信仰貌似存在一个差别:在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现新的规律;而宗教信仰活动,总是在不断重复宗教经典所述的故事和教义。
吴以义: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在不断回答相同的问题。为什么石头会掉向地面?亚里士多德问这个问题,一直到爱因斯坦还是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其实是在用不一样的符号系统解释同样的问题,不断地丰富它的回答。
李明洁:这恐怕和人类符号系统的设置有关。民间信仰使用的是日常语言系统,它无法超越语言的社会性即民众的公约性,所以只能使用相同的话语系统来表述,但表述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宗教文化当中一个非常显著的语言民俗,即宗教活动中各种形式的话语“互文现象”,就是宗教故事和教义的相互关联、重叠、重申等等。科学研究是超越日常语言系统的术语系统,不同学科都可以依据语言的任意性来不断地翻新本学科的符号,因而不同学科之间以及同一学科内部看上去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科学团队内部的语言规则造成的另一类“语言民俗”。但是如您所说,实际上也是在回应同样的问题。
吴以义:如果要谈科学研究和信仰的不同,唯一的一条,就是科学革命以后,认识方法有了改变,这是科学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原来的信仰系统是没有这个环节的,信就是信。证伪环节可以通过一个或一组实验来证明是或者不是。证明的前提是,我的“理性”在我的“信”之上,理性成了人类思维活动中唯一被认可的主导。如果是不合预期的,那么前提和假设就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革命把科学和信仰彻底地分开了,分水岭就是“验证”这个概念。
李明洁:宗教信仰是通过经典的反复阅读和阐释以及教友之间的一次次见证,从正面来强调信仰的,因为信仰的前提是“信”,所以需要的实际上只是对这个信念的重申、提醒和巩固。科学研究的前提则是“假设”,用程序设置来展现人类的理性。
吴以义:因此,宗教和科学实际上变成了两个领域。在宗教里面谈论验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在谈论它的系统中不存在的环节,因为宗教就是“信”。但是科学当中,它把信仰向后推了,我有预期,有完整的科学方法——观察、假设、推理、结论和结论的验证,这是个完整的科学程序。走完一个完整的科学程序,我才能证明我的假设是对的。马克思对这种验证有特别重要的阐发,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以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李明洁:这个后果会不会让很多的人脱离了宗教信仰?科学革命客观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后果呢?
吴以义:会啊,很多人认识了科学之后,就脱离了宗教信仰。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出发点和前提仍旧依赖一种信念,因为你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是一个先于一切的前提,而这件事情本身是无法用逻辑方法证明的。因为你证明了一个规律的存在,不能表明所有规律都是存在的。你永远是在用部分证全体。用部分来证明整体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这是一个隐含的而不是显明的问题,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当然是研究自然规律,但是你怎么知道自然规律是存在的呢?只有有了这个前提,你的科学逻辑才有意义。(作者:李明洁)
(复旦大学文博系崔璨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来源:2015年1月19日《文汇报》)
(编辑:霍群英)
1.来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
永久域名:iwr.cass.cnE-Mail:zjxsw@cass.org.cn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京ICP备0507273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