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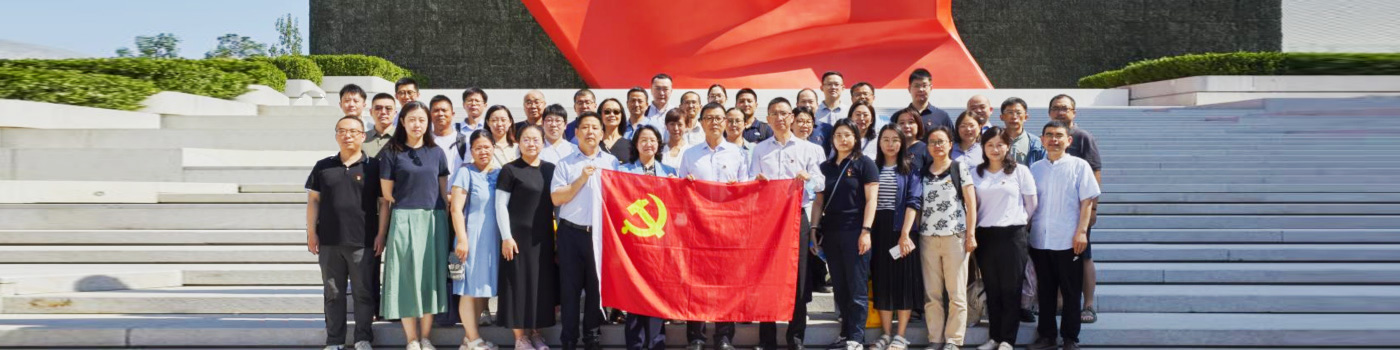
[内容提要]:1822年和1823年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出版了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圣经》汉语完整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开启了基督教新教翻译出版多达30余种汉语文言、白话和方言版本圣经的历史。在新约翻译上,二马译本都受到了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奠基性影响,其中马士曼译本还参考了马礼逊译本;在旧约翻译上,因其他事务产生的纠纷,导致了两人的各自独立翻译。在参考天主教译本的基础上,两个译本还开始了剥离天主教话语系统、创建基督教汉语圣经话语系统的尝试。
[关键词]:白日升译本;马礼逊;马士曼;汉译圣经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溯至唐朝。公元635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长安传教译经。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有“真经”、“旧法”(旧约)、“经留二十七部”(新约)和“翻经建寺”等语,表明7世纪时已有翻译圣经的活动。
16世纪,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圣经翻译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但传教的急迫需求让传教士采取了变通措施,先期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将圣经中的十诫编译成“祖传天主十诫”[2]。明末清初绝大部分天主教传教士则停留在对圣经的诠释和史实的叙述上,已有的圣经翻译尝试大多是按弥撒书或祈祷书的形式编译的。
但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确有翻译圣经的事实存在。1737年或1738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霍治逊(John Hodgson,1672-1755)在广州发现了一份圣经译稿,精心抄录后带回英国,汉语题名《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Quatuor Evangelia Sinice)。1739年9月,霍治逊将手抄稿呈赠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olane,1660-1753)[3],统一编入斯隆收藏的手稿部分(Sloane Manuscript)中[4]。
手抄稿共377面,全书以毛笔工整缮写,每叶两面,每面16行,每行24字,版面颇大,高27公分,宽24公分。它是依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5]翻译而成,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中的一章[6]。由于手抄稿没有译者姓名,当时仅知是某位天主教人士的译作,一直都不清楚更多的细节。[7]直到1945年10月,韦利克教授(Bernward H. Willeke,1913-1997)依据时间和内容考证出它是来华的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约1662-1707,音译巴设、巴塞)的译作,翻译时间约在1700年。[8]
然而这部长期以来不知作者的天主教圣经汉译手抄稿,却对百年之后基督教圣经翻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和影响。1822和1823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完整汉语《圣经》,即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出版。二马译本都不同程度的参考和依据了白日升译本,这是已经公认的事实[9],但学术界和教会界一直都没有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对比和研究。作为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二马译本是独立翻译,还是互相参考?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两个译本在翻译方面(如专名翻译、语言顺畅、文体采用等方面)是否有新的改变和发展?白日升译本仅有大部分新约,二马又是如何处理旧约的翻译?面对天主教的圣经译本,基督教是否有创建自己圣经汉语话语系统的考虑和努力呢?白日升译本对后来的天主教圣经翻译还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档案和文本文献,细密爬梳了上述问题,并对以往的成说提出修正意见。
一、二马新约译经:殊途同归——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
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地区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圣经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更是在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和工作下取得的。13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欧洲宗教改革先驱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30-1384)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圣经》首次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也相继问世。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奏响了宗教改革的序曲,从此信徒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各国基督教会期望脱离拉丁文圣经的桎梏,努力推进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对世界范围内的平民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帮助,基督教会则获得了重大发展。这也是基督教会远比天主教会热心圣经翻译的根本原因。
1792年,基督教传教运动创始人、英国浸礼会[10]牧师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发表宣言,极力倡导“传福音给每一个人”是基督给与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被视为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起点。1798年3月7日,英国北安普敦郡公理会牧师威廉·莫士理(William Moseley)发出公开信,提出将《圣经》译为汉语,请求“设立机构专责翻译圣经成为东方最多人的国家的语言”。[11]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允许传播基督教,而圣经译本可以渗入那些传教士无法到达的地区,因此翻译圣经是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最好方法。1800年,莫士理在题为《关于印刷及发行汉语圣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的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把《圣经》翻译成汉语提供给基督教传教士。[12]
1801年,威廉·莫士理怀着巨大喜悦在大英博物馆[13]发现了沉睡多年的白日升译本,立刻引起了大英圣书公会[14]的重视。1804年7月30日,英国伦敦会[15]决议,“翻译汉语圣经是有利于基督教的最重要目标之一”。[16]1807年,基督教第一位来中国大陆的传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受派之际,翻译“一部令人称赞的、忠于圣经的译本”就是他已经肩负的任务,他也为此进行了相关准备。在莫士理的引见下,马礼逊结识了从广东到伦敦学习英文的中国人容三德(Yong Sam-tak)。在容三德的帮助下,马礼逊将白日升译本全部抄录带到中国,作为翻译圣经的重要参考和基础,其手抄稿目前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1807年9月4日,马礼逊到达澳门。181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汉语书1000册,即《耶稣救世使徒传真本》(新约的《使徒行传》),后又陆续出版了《圣路加氏传福音书》(澳门或广州,1812年)、《厄拉氐亚与者米士及彼多罗之书》(澳门及广州,1813年)。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翻译完毕,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17]为名,刻印2000册,分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817年,马礼逊还在吗喇甲(今马六甲)刻印了《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
马礼逊曾详细地讨论过自己圣经翻译的原则,第一次是在1817年9月纪念他来华传教十周年之际,说明了他决定采取圣经翻译的风格及其理由。[19]第二次是在1819年11月底,他彻底完成全部圣经翻译之后,就整体圣经翻译进行了全面说明,详细说明了翻译时的问题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由,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考图书,依据的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圣经文本等,力图告诉大家他的汉语圣经文本的形成过程和原由。[20]
从马礼逊新约翻译的文本和专名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是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做了些调整和修改而成。对于自己译本与白日升译本之间的关系,马礼逊并不讳言,也多次提及。
我自由地修改,对我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做出补充:而且我深感愉快地记下从我未识其名的前人的努力中获得的好处。[21]
我冒昧对其作了修改,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我很愉快地记下我从那位不知名的前辈那里得到的教益。[22]
(1810年出版《使徒行传》后说)严格地说,只有序文才是我自己的作品。[23]我只是加以编辑而已。[24]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为,马礼逊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一半是他翻译的,另一半是他校正了白日升译本。[25]的确,如果没有白日升译本,对启程来华之际才开始学习汉语的马礼逊来说,在6年时间里翻译印刷圣经是不可想象的。
1823年,包括旧约和新约的《神天圣书》用木版雕刻方式全部刊印完毕。1824年5月,马礼逊亲自将《神天圣书》呈送给大英圣书会。“将圣经翻译成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所使用语言的成绩”使他获得了巨大荣誉。早在1817年,马礼逊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道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现在他又得到英皇乔治四世的召见,并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作为第一位来到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圣经译本对后来的众多基督教圣经译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他既不是第一位开始将圣经翻译成为汉语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是第一位出版完整汉语圣经的人。
在马礼逊翻译圣经之前,远在印度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已开始了圣经汉译的工作,甚至在马礼逊启程来中国之前已经开始了。[26]1799年,在传教士威廉·克里(时已在印度)号召的影响下,31岁的马士曼和威廉·华尔德(William Ward,1769-1823)来到印度。因浸礼会不属于英格兰的国教圣公会,马士曼等人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生活和工作颇觉困难,于是他们又转到丹麦统治下、位于加尔各答郊外的一个小镇——塞兰坡,组成了著名的“塞兰坡三人组”(Serampore Trio),建立了布道站、教堂,并逐渐发展出以印刷与出版为主的传教方法和路线。1804年4月,威廉·克里等人共同签署了翻译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东亚语文圣经的计划。他们三人以建立了高效的印刷所、翻译印刷众多译本的《圣经》而著称于世,从1801年出版孟加拉语《新约》开始,到1832年为止,塞兰坡教会印刷站(Serampore Mission Press)共出版了多达40种语文、21万余册的宗教与世俗书刊[27],这是至今仍然让人震惊和感叹的工作成绩。
1800年,威廉·克里在塞兰坡建立了第一所教堂;同年,有“东方牛津”之称的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一译英印学院)在加尔各答成立。1804年,在威廉堡学院副院长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1815)的发现和邀请下,生长于澳门的亚美尼亚裔青年拉撒(Joannes Lassar,一译拉沙,1781-1835?)获聘为威廉堡学院汉语教授,并加入了与马士曼合作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的计划。[28]拉撒原本是商人,携带大批茶叶到加尔各答经商,却遇上茶叶价格大幅下跌而陷入困境。他与马士曼之间的“合作”并没有立即开始,1804年出版的汉语圣经(部分《马太福音》和《创世记》),是由拉撒译自亚美尼亚语圣经。[29]
在拉撒的帮助下,经过其他几个人的校阅和几易其稿,马士曼于1810年以木刻雕版印刷了《此嘉语由于[口孖][口挑]著》(《马太福音》),1811年刊印了《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马可福音》)。马士曼远在印度,没有参考任何其他圣经汉译本,以当时局面,他手中有多少汉语参考书都是问题,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其译文晦涩难明不顺,亦不难想象;人名地名、神学名称,完全杜撰,生搬硬造。
马士曼《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1章1-8节(1811年)[30]
1嘉音之始。乃从意囌[口记]唎[口时]喥神之子也。2仿于圣人所著之语。指视我令使者于尔之前。伊则除清尔道于尔之前也。3人呼。声在僻处。曰。除清天主康衢。又整齐其径。4[口玉][口晏]于僻处。蘸淬。而宣扬。改过兼恕罪之蘸者。5意[口路]唦啉。并[口玉][口地]哑一国俱往于他。被他蘸于[口欲]噋之河。而认其罪矣。6[口玉][口晏]服骆驼之毛。束皮带于腰间。而食蚱蜢。兼野蜜。7宣扬曰。于我之后来。一名强过我者。伊之鞋带无缘俯解也。8确是我蘸尔等于水。然他必于神魂于蘸尔也。
从马士曼翻译的文本和专名中可以看出,他将“福音”译为“嘉音”、“耶稣基督”译为“意囌[口记]唎[口时]喥”、“约翰”译为“[口玉][口晏]”、“耶路撒冷”译为“意[口路]唦啉”、“约旦河”译为“[口欲]噋之河”、“犹太”译为“[口玉][口地]哑”、“圣灵”译为“神魂”、“洗”译为“蘸”,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采用了音译加口字旁的方法,与后来的圣经专名翻译差异极大,与今天通用的圣经专名更没有任何相同相近之处。
1813年,马士曼在塞兰坡出版了《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这是第一本铅字活版印刷的汉语书籍,比国内最早的活版印刷汉语书籍早了9年[31],其在汉语印刷出版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马士曼也高兴地认为用活版铅字印刷《圣经》汉语译本,是他们取得的一项非凡的成就,不但灵活印刷,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了。[32]这部书的汉语翻译水平显著提高,文笔变得较为通顺,人名、地名、神学专名与马士曼1811年版《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根本不同,马士曼1815-1821年版《新约》的翻译风格和专名译法也可视为在本书的基础上的继承和修订。在短暂的两年时间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呢?
现抄录白日升译本《约翰福音》、马士曼《若翰所书之福音》1章29-39节,列出两个版本与基督教圣经汉译最大集成《和合本》[33]和天主教圣经汉译最大集成《思高本》[34]的人名、地名和神学等专名,以便比较。
白日升《约翰福音》1章29-39节(1700年前)[35]
29次日若翰视耶稣游曰。此乃神之羔。此乃除世罪者。30且曰其先我已在。31我素不识之。而特来付水之洗。著之于依腊尔焉。32又证曰余已见圣神如白鸽自天降而居其上。33余素弗识之。然使我付水洗者。其语我曰。尔见圣神所临立者。此乃以圣神洗者也。34余已见而证其为神之子也。35他日同若翰有二徒。36若翰视耶稣游。曰。此乃神之羔。37徒闻言即随耶稣。38耶稣回视其从。问之曰。尔等何寻。答之曰。师尔。何居。39曰尔等来且看。伊遂来而看其立且比日同居焉。为其时乃几十时也。
马士曼《若翰所书之福音》1章29—39节(1813年)[36]
29次日若翰见耶稣来至其处曰。瞻除世罪之神羔。30余前所言其来我之后尊举在我之先因其先我而有即此人也。31余未知之。但我来以水蘸淬使其明于依腊尔之辈。32若翰作此证曰。我见圣风如鸽自天降下坐其上。33我未知他但其遣我蘸人嘱我曰。见圣风降而止其上其将以圣风蘸人者是也。34我已见而证之其为神子也。35次日若翰惟与二徒伫立。36见耶稣行游乃曰。瞻神之羔。37其二徒闻而随之。38耶稣回顾见此二徒紧随。曰。尔觅何人。曰。卑罅译云师也。汝居何处。39耶稣曰。尔来观之。观毕其处。是日同处将六时。
表1 白日升本、马士曼本、和合本、思高本《约翰福音》1章29-39节专名
| 白日升本 | 马士曼本 | 和合本 | 思高本 |
| 原文无篇名 | 若翰所书之福音 | 约翰福音 | 若望福音 |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 若翰 | 若翰 | 约翰 | 若翰 |
| 耶稣 | 耶稣 | 耶稣 | 耶稣 |
| 罪 | 罪 | 罪孽 | 罪 |
| 神 | 神 | 神/上帝[37] | 天主 |
| 洗 | 蘸 | 施洗 | 施洗 |
| 依腊尔 | 依腊尔 | 以色列 | 以色列 |
| 圣神 | 圣风 | 圣灵 | 圣神 |
| 师 | 卑罅/师 | 拉比/夫子 | 辣彼/师傅 |
用中国语言文字表达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的基督教概念,是基督宗教翻译史上最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内容,必定要通过创造、借用、转化、意译、音译、音意合璧译等方式,才能建立起基督教的汉语话语系统。传教士们采用了大部分意译、个别音译的办法,其中万物主宰始终都采用“神”,借用中国传统词汇表达了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基督教神学概念“圣人”、“罪”、“恕”、“赦”;创造新词汇来表达新概念,如“预知”、“先知”、“福音”、“嘉音”、“圣灵”、“神风”;而“蘸”、“施洗”则是浸礼会与新教其他差会之间在神学上的最基本和最本质差异。
通过文本和专名对比可以看出,马士曼译本与白日升译本之间的高度相似表明了导致马士曼译本巨大变化的原因。原来,马礼逊于1809年将白日升译本抄写一份寄给了马士曼[38],马士曼亦承认自己参考借鉴了白日升译本[39]。马士曼也曾详细描述过他翻译圣经的过程,即他和儿子、助手拉撒、他的汉语教师及其他中国人是如何互相交叉斟酌译文的用字遣词,如何不辞辛苦地数十次易稿,才产生出他的译作。[40]
1815-1822年,马士曼用活版铅字出版了《新约》。1816-1822年间,《旧约》也逐渐翻译完成。1822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用活版铅字印刷了五卷本的《圣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汉语圣经,奠定了马士曼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地位。1823年5月,马士曼的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1794-1877)将第一本汉语《圣经》呈送大英圣书会。[41]除圣经外,塞兰坡教会印刷站还出版过他的博士论文、第一部英译《论语》(The Work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st, with a Translation,1809)和研究汉语的字形、发音、语法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又名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42]。马士曼的《圣经》、《论语》和《中国言法》是以出版英文和梵文书籍为主的塞兰坡教会印刷站出版过的仅有的三种汉文书籍(《论语》为英汉对照,《中国言法》中有大量的汉字、词和语句)。马士曼还与他儿子一起创办了印度历史上最早的英文报纸《镜报》(Sumachar Durpon, or Mirror of News)。马士曼出版完整圣经汉译本和将其呈送大英圣书会,均比马礼逊早一年,且用活版铅字印刷,印刷和纸质比马礼逊译本好了许多。
二、二马的新约译经:抄袭说之辨
两位英国传教士分别在印度和中国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基督的名最终被全部知晓”的神圣事业,在拓展基督教传教新领域方面,马礼逊和马士曼有两项工作是完全相同的,即翻译圣经和编写汉语语法书。
二马的圣经译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关于这点,历史上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二马译本都是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形成,这是两个译本有如此众多相同的原因,但两个译本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独立完成,不存在抄袭问题。[43]二是抄袭之说,即马士曼译本抄袭了马礼逊译本,而且此说在他们生前就已经存在了。
抄袭之说最初源自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之口,见于1815年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人因《通用汉言之法》发生公开指责之后,1818年7月18日勃格博士(Rev. Dr. Bogue)给马礼逊的信:
米怜先生给我讲述了他们(指马士曼和拉撒)的译作似乎确可证明是抄袭自您的(taken from yours)。……我的意见是,您应该冷静而果断地为自己申辩,力证译作是您的,并指出所有剽窃之处(expose all plagiarism)。他们不仅把您的错字照抄,且把刻字工错漏的字亦同样漏去,这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欺骗。……您要讨回的公道,就是要把问题清楚向基督徒世界讲明。[44]
此后,跟马礼逊学习过汉语、伦敦大学中国语文及文学教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修德(Samuel Kidd,1799-1843)在他著名的《评马礼逊博士的文字事工》(Critical Notices of Dr. Morrison’s Literacy Labours)长文中,从神学专名、人名地名、译文文体风格等专业角度详细分析和评价了马礼逊在文字出版方面的贡献,该文也认为二马的圣经翻译相似程度太高,存在不解之处。
在某些章节上,马士曼和马礼逊的译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以“蘸”代“洗”及一两个不重要的字有所不同外,以致公正的人都会以为那是逐字照搬(copied verbatim);新约从头到尾,类似的雷同委实过多,让人难以相信那纯属巧合。[45]
仔细对比二马的《新约》文本可知,二马译本与白日升译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表明它们都是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而成。但另一方面,无论在语句行文、遣词造句上,还是在人名、地名、神学专名的翻译上,二马译本之间的相似程度都远远高于它们与白日升译本的相似程度。马士曼和马礼逊分别在印度和中国进行翻译,终身没有见过面,即便两人都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两个译本如此相似亦是蹊跷。
现抄录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的《约翰福音》1章14-20节,并列专名表进行对比。
白日升《约翰福音》1章14-20节(1700年前)[46]
15若翰证指之号曰。此乃吾素所云。将来于我后者。已得有于我前也。盖先我在。16且吾众自其盈满。而已受矣恩亦代恩。17盖报律以每瑟而授。宠及真以耶稣基利斯督而成也。18从来无人得见神。独子在父怀者。其乃已述也。且曰其先我已在19且如达人自柔撒冷遣铎德与勒微辈问若翰。尔为谁。20其出此证词。且认而不讳。认曰。我非基利斯督者。
马礼逊《圣若翰传福音之书》1章14-20节(1813年)[47]
14其言变为肉而居吾辈之中、且吾辈见厥荣、夫荣如父之独生、而以宠以真得满矣。15若翰证指之呼曰、此乃彼余所说及者、其后余而来者、即荐先我、盖其本先我、16又由其之满我众受宠于宠焉。17盖例即以摩西而已施、乃宠也真也以耶稣基督而来矣。18无人何时而见神、惟独生之子在父怀其述知之也。19且此为若翰之证、如大人自耶路撒冷既遣祭者与唎味辈问之尔为谁、20其即认而不讳、乃认曰、我非弥赛亚者。
马士曼《若翰传福音之书》1章14-20节(1815-1822年)[48]
14其言变为肉而居我等之中。且我等睹厥荣。夫荣如父之独生得满以宠以真矣。15若翰证及之呼曰。此即他。我所道及的。其后我而来者已荐先我。盖其本先我。16又由其之满我众受宠于宠焉。17盖律见施以摩西。惟宠也真也来以耶稣基利士督。18无人何时而见神。惟独生之子在父怀其述知之也。19且此为若翰之证。时如大人自耶路撒冷使祭者与利未辈问之尔为谁。20其认而不讳。乃认曰。我非其基利士督。
表2 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和合本、思高本《约翰福音》1章14-20节专名
| 白日升本 | 马礼逊本 | 马士曼本 | 和合本 | 思高本 |
| 原文无篇名 | 圣若翰传福音之书 | 若翰传福音之书 | 约翰福音 | 若望福音 |
| 原文无14节 | 言变为肉 | 言变为肉 | 道成了肉身 | 圣言成了血肉 |
| 若翰 | 若翰 | 若翰 | 约翰 | 若翰 |
| 恩亦代恩 | 受宠于宠 | 受宠于宠 | 恩上加恩 | 恩宠上加恩宠 |
| 律 | 例 | 律 | 律法 | 法律 |
| 每瑟 | 摩西 | 摩西 | 摩西 | 梅瑟 |
| 宠 | 宠 | 宠 | 恩典 | 恩宠 |
| 耶稣基利斯督 | 耶稣基督 | 耶稣基利士督 | 耶稣基督 | 耶稣基督 |
| 神 | 神 | 神 | 神/上帝 | 天主 |
| 如达人 | 如大人 | 如大人 | 犹太人 | 犹太人 |
| 柔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 勒微辈 | 唎味辈 | 利未辈 | 利未人 | 肋未人 |
| 基利斯督 | 弥赛亚 | 基利士督 | 基督 | 默西亚 |
再抄录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的《歌罗西书》1章1-6节,并列专名表对比。
白日升《福保禄使徒与戈洛所辈书》1章1-6节(1700年前)
1保禄奉神旨为耶稣之使徒。且弟氏末陡2与诸在戈洛所弟兄圣信于耶稣基督者。愿尔等得恩宠。平和。由神我等父由主耶稣基督也。3吾感谢神及吾主耶稣基督之父。而为汝曹常祈祷。4因闻汝向基督耶稣之信。且汝致诸圣之爱。5为俟尔于天之望。汝所闻于福音之真言者。6夫福音至于汝曹如于普天下。且到处衍化广行。如尔间自汝闻真言而识神恩之日焉。
马礼逊《圣保罗使徒与可罗所书》1章1-6节(1813年)
1保罗奉神旨为耶稣基督之使徒、且吾弟弟摩氏、2与诸在可罗所弟兄、圣信于耶稣基督者、愿尔等得恩宠、平和、由神我等父、由主耶稣基督也、3吾感谢神、及吾主耶稣基督之父、而为汝曹常祈祷、4因闻汝向基督耶稣之信、且汝致诸圣之爱、5为放在俟尔于天之望、汝所先闻于福音之真言者也。6夫福音至于汝曹、如于普天下、且到处衍化广行、如尔间、自汝闻言而真识神恩之日焉。
马士曼《使徒保罗与可罗所辈书》1章1-6节(1815-1822年)
1保罗奉神旨为耶稣基督之使徒。且弟弟摩低。2与在可罗所圣信与耶稣基督之诸弟兄。愿汝辈获恩宠平和。由神吾等父。及主耶稣基督也。3予自闻汝之信向基督耶稣。及汝之爱致诸圣。4吾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之父。且为汝曹恒祷。5为汝置于天之望。即汝曩所闻于福音之真言者也。6夫福音至于汝曹如于普天下。且到处结实如汝闻。自汝闻言。真识神恩之日矣。
表3 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和合本、思高本《歌罗西书》1章1-6节专名
| 白日升本 | 马礼逊本 | 马士曼本 | 和合本 | 思高本 |
| 福保禄使徒 与戈洛所辈书 | 圣保罗使徒 与可罗所书 | 使徒保罗 与可罗所辈书 | 歌罗西书 | 哥罗森书 |
| 保禄 | 保罗 | 保罗 | 保罗 | 保禄 |
| 神 | 神 | 神 | 神/上帝 | 天主 |
| 使徒 | 使徒 | 使徒 | 使徒 | 宗徒 |
| 氏末陡 | 弟摩氏 | 弟摩低 | 提摩太 | 弟茂德 |
| 戈洛所 | 可罗所 | 可罗所 | 歌罗西 | 哥罗森 |
| 恩宠 | 恩宠 | 恩宠 | 恩惠 | 恩宠 |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 耶稣(1节) | 耶稣基督(1节) | 耶稣基督(1节) | 基督耶稣(1节) | 基督耶稣(1节) |
| 耶稣基督(2节) | 耶稣基督(2节) | 耶稣基督(2节) | 基督(2节) | 基督(2节) |
| 耶稣基督(3节) | 耶稣基督(3节) | 基督耶稣(3节) | 耶稣基督(3节) | 耶稣基督(3节) |
| 基督耶稣(4节) | 基督耶稣(4节) | 耶稣基督(4节) | 基督耶稣(4节) | 基督耶稣(4节) |
再列表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和合本《马太福音》1章1-23节专名对比。
表4 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和合本《马太福音》1章1-23节专名
| 白日升本 | 马礼逊本 | 马士曼本 | 和合本 | 思高本 |
| 原文无篇名 | 圣马宝传福音书 | 使徒马宝传福音书 | 马太福音 | 玛窦福音 |
| 阿巴郎 | 亚伯拉罕 | 亚百拉罕 | 亚伯拉罕 | 亚巴郎 |
| 达未 | 大五得 | 大五得 | 大卫 | 达味 |
| 耶稣基利斯度 | 耶稣基利士督 | 耶稣基利士度 | 耶稣基督 | 耶稣基督 |
| 生谱 | 生谱 | 生谱 | 家谱 | 族谱 |
| 撒落蒙 | 所罗门 | 所罗门 | 所罗门 | 撒罗满 |
| 玛利亚 | 马利亚 | 马利亚 | 马利亚 | 玛利亚 |
| 若瑟 | 若色弗 | 若色弗 | 约瑟 | 若瑟 |
| 圣神 | 圣风 | 圣风 | 圣灵 | 圣神 |
| 先知 | 先知 | 先知 | 先知 | 先知 |
| 厄慢尔 | 以马奴耳 | 以马奴耳 | 以马内利 | 厄玛奴耳 |
| 神 | 神 | 神 | 神/上帝 | 天主 |
| 如达 | 如氐亚 | 如氐亚 | 犹太 | 犹大 |
| 白冷 | 毕利恒 | 毕利恒 | 伯利恒 | 白冷 |
| 柔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 |
通过以上文本和专名的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二马译本与白日升译本非常相似,二马译本是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专名翻译上,马礼逊译本与白日升译本的相同率分别是23%(表2)、58.3%(表3)和20%(表4);马士曼译本与白日升译本的相同率分别是30.8%(表2)、41.7%(表3)和20%(表4)。二马译本之间的相同程度高于它们与白日升译本,二马译本的专名更是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相同率达61.5%(表2)、66.7%(表3)和80%(表4)。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二马的《新约》都不能称之为独立翻译,都严重依赖和参考了白日升译本。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二马译本又有所修订和创造,二马之间始终都有沟通,马士曼译本更多地参照了马礼逊译本。
1809年,马礼逊主动将白日升译本抄写一份给了马士曼。得到白日升译本后,1813年,马士曼出版了有巨大改变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在随后几年里,马士曼又得到了马礼逊译本[49],它是“由不同的朋友当作中文书籍寄给我的”,马士曼还为马礼逊没有亲自将自己的著作寄给他而感到不悦。[50]这是1815年马礼逊公开指责马士曼抄袭他的《通用汉言之法》后,马士曼于1816年12月13日致浸礼会的公开信所承认的。由马士曼公开信的时间可知,马士曼拿到的是马礼逊1813年木刻雕版印刷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新约》),马士曼完全有“参考修订”的可能。对此,马士曼也是承认的。
一位朋友赠送了一部马礼逊弟兄刊印的版本给我们,每当需要时,我们也认为有责任查阅它,当我们看到它显然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拒绝对我们的原著进行修改是合理的。在翻译圣经如此重要的工作中,如果因为虚荣和愚蠢,自以为可以重现原文的想法,而拒绝参考他人的努力成果,一切就会变得令人失望,这也是放弃了对一本完美无瑕的圣经译本的盼望。[51]
1815-1822年,马士曼刊印了再次修改后的定稿版《新约全书》。将1813年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和定稿版《新约全书》中的《若翰传福音之书》比较可知,马士曼的定稿版离白日升译本更远,与马礼逊译本更相似了。
现抄录马礼逊1813年版《圣若翰传福音之书》和马士曼1815-1822年版的《若翰传福音之书》1章29-39节,并列专名表对比。马士曼1813年版的《若翰所书之福音》1章29-39节前文已录,此不再重复。
马礼逊《圣若翰传福音之书》1章29-39节(1813年)
29次日若翰见耶稣来向之而曰、观神之羔、取去世之罪之者与。30此乃吾素所云、将来于我后者、而已有于我前也、盖其本前我而在焉。31又余素弗识之、而特来付水之洗、现著于以色耳以勒之人也。32若翰又证曰、余既见圣风如白鸽焉、自天降而居其上、33余素弗识之。然使我付水洗者语我曰、尔见圣风所临居者此乃以圣风而洗者也。34余已见而证其为神之子也。35又其次日若翰立偕厥门徒二位。36若翰视耶稣游时曰、此乃神之羔者。37二徒闻言即随耶稣。38耶稣回视其徒随后问之曰、尔等何寻也。答之曰、啦吡即是译言师、尔何居。39曰尔来且看。伊遂来而看其居之所、又彼日同居焉。其时乃约十时也。
马士曼《若翰传福音之书》1章29-39节(1815-1822年)
29次日若翰见耶稣来向之。而曰。观神之羔取去世之罪者与。30斯即吾素所云。将来于我后者乃在于我前也。盖其本前我而在焉。31又吾素弗识之。而特来施水之蘸以示之于以色耳勒辈也。32若翰又证曰。吾见圣风如鸽焉自天降而止其上。33吾素弗识之。然使我施水蘸者谓我曰。尔见圣风所临止者此乃以圣风而蘸者也。34吾已见而证其为神之子也。35又其次日若翰立偕厥门徒二位。36若翰见耶稣游时曰。观神之羔与。37二徒闻言即随耶稣。38耶稣回顾而见伊等随之。问伊曰。尔等何寻也。答之曰。啦吡。即是译言师。尔何居。曰。39尔来看。伊遂来而看其居之所。彼日偕处焉。其时乃约十时也。
表5 白日升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1813年)、马士曼本(1815-1822年)、
和合本、思高本《约翰福音》1章29-39节专名
| 白日 升本 | 马礼逊本 (1813) | 马士曼本[52](1811) | 马士曼本(1813) | 马士曼本 (1815-1822) | 和合本 | 思高本 |
| 原文无篇名 | 圣若翰传福音之书 | 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 | 若翰所书之福音 | 若翰传福音之书 | 约翰福音 | 若望福音 |
| 福音 | 福音 | 嘉音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福音 |
| 若翰 | 若翰 | [口玉][口晏] | 若翰 | 若翰 | 约翰 | 若翰 |
| 耶稣 | 耶稣 | 意囌 | 耶稣 | 耶稣 | 耶稣 | 耶稣 |
| 神 | 神 | 神 | 神 | 神 | 神/上帝 | 天主 |
| 罪 | 罪 | 罪 | 罪 | 罪 | 罪孽 | 罪 |
| 洗 | 洗 | 蘸 | 蘸 | 蘸 | 施洗 | 施洗 |
| 依腊尔 | 以色耳以勒 |
| 依腊尔 | 以色耳勒 | 以色列 | 以色列 |
| 圣神 | 圣风 | 神魂 | 圣风 | 圣风 | 圣灵 | 圣神 |
| 师 | 啦吡/师 |
| 卑罅/师 | 啦吡/师 | 拉比/夫子 | 辣彼/师傅 |
经过多种文本的对比考辨可以确认,在新约翻译上,马士曼不是完全独立的翻译,非常严重的参考了马礼逊译本。除了坚持浸礼会与基督教其他宗派最基本神学差异而形成的“蘸”字外,马士曼1815-1822年定稿本的《约翰福音》1章29-39节修改了仅有的两个不同于马礼逊、源于白日升译本的专名——依腊尔、卑罅,而且几乎修订了所有语句和顺序。
英国牛津大学Regent’s Park学院安格斯图书馆的收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旁证。安格斯图书馆亦是英国浸礼会的档案馆,这里收藏了英国浸礼会所有传教士和教会事务的档案,包括浸礼会差派到国外的传教士的档案和书籍,如马士曼的档案资料和圣经译本,以及浸礼会后来的圣经汉译修订本,即高德译本(1851)[53]、怜为仁译本(1866)[54]、胡德迈译本(1867)[55]等。笔者只看到了马礼逊的《新约》译本,而没有看到《旧约》译本。
马礼逊同时也有马士曼的《新约》译本,这是马士曼1815年寄给马礼逊的。[56]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马礼逊收藏中可证明,马礼逊的确收藏有马士曼译本。[57]不过马礼逊在翻译中似乎没有怎么使用它,这从马礼逊的修订本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可以看出。
三、二马的旧约译经:各自独立翻译
白日升译本只有新约的大部分,而没有旧约。在没有参照基础的前提下,二马是如何进行翻译工作的?是互相沟通、参照,还是独立翻译呢?
1813年,马礼逊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出版完毕。1813年7月,米怜到达中国,协助马礼逊翻译旧约,米怜翻译了《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1814年,出版了《旧遗诏书第一章》(《创世纪》第1章)的单张。1819年11月25日,旧约全部译成。[58]1819-1823年,陆续刊印了木刻雕版的《旧约》。1823年,马礼逊以《神天圣书》为名,一次性刊印了新约和旧约,共21册。
1816年,马士曼的旧约译文完成,1816-1822年陆续刊印了活版铅字的《旧约》,1816年刊印《创世纪》,1817年刊印《摩西五经》,1818年刊印《约伯记》至《雅歌》,1819年刊印《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1822年刊印《约书亚记》至《以斯贴记》。[59]
现抄录马礼逊1814年版、马礼逊1819-1823年版、马士曼1816-1822年版《创世纪》1章1-13节对比。
马礼逊《厄尼西士之书》1章1-13节(1814年)[60]
1神当始原创造天地者。2且地无模而虚暗。在深者而上。而神之风摇动于水面上。3神曰。为光者即有光者也。4且神视光者为好也。神乃分别光暗也。5光者神曰日。暗者其曰夜。且夕旦为首日子也。6神曰申开者在水之中则分别水于水。7神成申开者而分别水在申开者之上于水在申开者之下而已。8申开者神名之天。且夕旦为次日也。9又神曰。天下之水集一处。且干上发现而已。10干土者神名之地。集水者其名洋。而神视之为好也。11神曰地萌芽菜草发种随其类。树在地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已。12则地萌芽又菜发种随其类。树亦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神视之为好。13且夕旦为第三日也。
马礼逊《创世历代传》1章1-13节(1819-1823年)[61]
1神当始创造天地也。2时地无模且虚。又暗在深之面上。而神之风摇动于水面也。3神曰。由得光而即有光者也。4且神视光者为好也。神乃分别光暗也。5光者神名之为日。暗者其名之为夜。且夕旦为首日子也。6神曰。在水之中由得天空致分别水于水。7且神成天空而分别水在天空者之上于水在天空之下而即有之。8其空神名之为天。且夕旦为次日也。9又神曰。由天下之水得集一处。且干土发现而即有之。10干土者神名之为地。集水者其名为洋。而神视之为好也。11神曰。由地萌芽菜草发种随其类。树在地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即有之。12则地萌芽又菜发种随其类。树亦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神视之为好。13且夕旦为第三日也。
马士曼《神造万物书》1章1-13节(1816年)[62]
1原始神创造天地。2地未成形。阴气蕴于空虚幽邃之内。神风运行水上。3神曰光。而遂光焉。4神见光好。以暗分之。5神呼光为昼。呼暗为夜。斯朝暮乃首日之朝暮也。6神命水中之元气分水。7而元气辄分上下。8爰号清气为天。此朝夕乃第二日之朝夕也。9神曰。天下之水。注于一处。以显陆地。果遂显焉。10神呼陆为地。水注处为海。神见此美。11曰。地生草。树生果。各从其类而结实。果如其嘱。12凡地中植物各依类而生种。树亦因之而结实。实在果中。神见美之。13此晨昏乃第三日之晨昏也。
通过文本对照可发现,马礼逊译本和马士曼译本相差很大,互相借鉴参考的可能性很小。马士曼译文更为通达顺畅,甚至可见汉语修辞和韵律的端倪。马礼逊的翻译除篇名从音译的《厄尼西士之书》修改为意译的《创世历代传》、增加了句读外,两个译文内容基本没有变化,这或许可以从马礼逊此时正忙于编纂《英华字典》和《通用汉言之法》中得到解释。
《创世纪》乃叙述性文体,下面再选录更具文学性的《诗篇》来比照,应该更具有说服力。
马礼逊《神诗书传》1卷1篇(1819-1823年)
1人不行无敬神之谋、不立在罪者之路、不坐戏侮者之椅、则有福矣。2其人即喜于神主之诫、且日夜念之。3其似栽河傍之树、当时结实、而叶永不落也。其凡所行即幸得成矣。4恶人不如此、乃如干草风所吹去。5且恶者不能当审时。罪者亦不能在善之会也。6盖神明知义人所行、乃无畏神者所行必被全坏矣。
马士曼《大五得诗》1卷1篇(1818年)
1福矣其人不行恶者之谋。不立于罪辈之道。不坐于诮辈之位。2乃悦于耶贺华之律而于厥律昼夜想度。3必得如植近河漘之树。依时结实。叶亦不枯。其之所行必遂。4而恶者则不然。乃如被风吹去之糠。5故恶者不敢立于审判之际。罪辈不敢立于义者之会。6盖耶贺华认义者之道。而恶者之道必败。
除“大五得”(大卫)这个在新约出现过的人名相同外,整个篇章中没有相同的译名,语句顺序也完全不同。尤其对重要专名“耶贺华”(马士曼版)和“神主”(马礼逊版)的不同译法,反映出他们之间的独立翻译。笔者还对二马译本的《箴言》1章1-8节、《阿摩司书》1章、《民数记》1章进行了对比,结论依然如此。
在旧约翻译上,二马之间为什么不再互相沟通、参考了呢?这从他们因《通用汉言之法》发生的公开争执中可以找到答案。
二马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一个在印度,一个在澳门,困难到难以沟通和交流的程度。对当时交通困难的想象,经常成为人们日后对事实进行判断的逻辑前提。虽然交通有困难,但每年两个贸易季节,总有从欧洲出发的商船经印度到广州,二人通过这个渠道可以有一些交流,这种方式的沟通从马礼逊刚到中国就开始了。马礼逊初抵中国后,为打开传教局面和获取信息,主动与在亚洲各地的传教士进行联系,在他发出的众多信件中,就有寄给马士曼的信件。1809年,他还主动抄录白日升译本给马士曼,以帮助他提高翻译圣经的水平。但由于沟通渠道不稳定,马礼逊在陆续收到别人的回复之时,却未收到马士曼的任何消息,他逐渐怀疑对方是故意不理,使他心中不悦。直到1810年1月,马礼逊收到马士曼一封“友善而诚恳”的信后,才解除了他的心中疑惑。作为代表传教团体利益、力争实现“最早最先”的竞争对手,此后二马尽管保持联系,但实际行动中却都有保留,互信程度也很薄弱,不给对方以切实有份量的帮助,如代购中文图书、纸张等。双方基本上都处于克制自己心态,努力加强自身的中文能力和拓展其他教务的状态。从苏精先生基于伦敦会档案资料的论文分析可知,实际上这是伦敦会和浸礼会两个传教团体长达20年的竞争所致。[63]
1809年,马礼逊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汉语语法的书籍——《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初稿,1811年经过当时英国公认汉语水平最高、曾随马戛尔尼使团来过中国的斯当东爵士(George Staunton,1781-1859)的审查后准备出版。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1812年初将文稿送到加尔各答,建议印度总督出版,这是塞兰坡印刷业发达和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出版印刷导致的结果。将近两年半后,即1814年,马礼逊收到了决定由塞兰坡教会印刷站出版的通知。[64]不料书还没有出版,马礼逊却在1815年收到了马士曼寄来的内容、功能类似的《中国言法》,它是1814由塞兰坡教会印刷站出版的马士曼撰写的研究汉语的字形、发音、语法的书籍。
1815年7月,盛怒之下的马礼逊写信公开指责马士曼抄袭他的《通用汉言之法》,言辞激烈地要求教会给予公开说法。[65]这些公开指责信,经过二马所属的差会——伦敦会和浸礼会的传递,终于到达马士曼的耳朵里。一石击起千重浪,一怒之下的马士曼撰写了长篇辩驳信,在否认自己抄袭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的同时,反而控告马礼逊在圣经翻译上抄袭了白日升译本,指责马礼逊的圣经翻译根本没有注明是在他人译本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又如何能指责别人的抄袭呢?[66]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马士曼详细对照了白日升译本和马礼逊1810年出版的《耶稣救世使徒传真本》,发现全书共70叶,约21500余字,而马礼逊只更动了1113字,其中还包括重复出现的人名、地名在内。[67]1815-1817年间,双方都多次向各自差会撰写了长篇申辩信,以示自己的清白、无辜,成为当时教会内颇为著名的一段公案。
1817年后,马礼逊和马士曼都不再进行公开争论,急于完成圣经翻译和其他工作,领先出版第一部汉语圣经。同时两人也没有了沟通联系的客观必要,马士曼除忙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圣经翻译外,还要主持当地教会学校等多项事务;马礼逊忙于《英华字典》的编辑和其他教务工作的开展。这时东印度公司已在澳门建立了印刷所,伦敦会则在马六甲建立了包括印刷所在内的布道站,马礼逊的著作也不必到塞兰坡请人帮忙出版印刷了。经过10余年的经营,二马在印度和中国的传教事业都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发展,对他人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
自从1815年发生公开争执之后,两人出版的书籍、译稿等都不再寄给对方。马士曼和马礼逊的《旧约》分别于1816年和1819年11月译成,印刷于1816-1822年和1819-1823年间,彼此已经没有参考的可能,这构成了二马旧约翻译相对独立的原因。虽然最后马礼逊也获得了马士曼译的圣经,但这已经是1822年之后的事情,马礼逊的旧约也早已译成并在印刷之中,已经不需要或不愿意参考马士曼译本了。
在二马为《通用汉言之法》发生公开争执后,才引发了马士曼抄袭马礼逊《圣经》的说法,而事件当事人马礼逊始终只指责马士曼抄袭了他的语法书,却没有指责过马士曼抄袭他的圣经。这或许从马礼逊的圣经译本是基于白日升译本而成,从某种角度来说,马礼逊译本也可称之为“抄袭”了白日升译本,指责理由不甚充足中找到答案。远在19世纪早期,人们对所谓的“抄袭”还是“引用”、“参照”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严格的学术规范。
四、余论
有学者分析了大英圣书会1822年《第十八届年报》公布的塞兰坡和广州的出版情况表,认为马士曼翻译圣经开始得比马礼逊早,出版时间早,尤其是修德所举的存在相似之处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均是马士曼翻译和出版在先,马士曼抄袭马礼逊在逻辑上难以成立。[68]另有学者认为,马礼逊1810年才开始翻译圣经,而1810年马士曼已经出版了圣经章节的译本,故而马礼逊有可能参照了马士曼译本。[69]的确,马士曼在1810年已出版《此嘉语由于[口孖][口挑]所著》(《马太福音》)、1811年已出版《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马可福音》)、1813年已出版《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但通过文本对比考证可知,1811年的《马可福音》、1813年的《约翰福音》与1815-1822年最终定稿本之间经历了许多变化和修订。英文文献中都是完全相同的“Gospel According to Mark”(马可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John”(约翰福音),但此“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远不是彼“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仅凭英文文献进行逻辑推理,没有文本的对比考证似有不足。
另有学者认为二马都以白日升译本为蓝本,认为二人的“译经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抄袭之说似无从谈起”[70],也不甚正确。他们的新约翻译都是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开始的,但并非独立进行,马士曼在得到马礼逊的新约译本后,又再次进行了修订;《旧约》翻译由于没有可参考依据的共同文本,两人都必须进行创作,而二人因其他事务而出现的指责和隔阂,使他们失去了互相参考沟通的机会,形成了独立翻译的局面。
二马译本开启了中国人拥有完整汉语圣经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由于马礼逊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圣经译本得到了更多的重视。马礼逊在中国进行翻译工作,可能会得到更多优秀中国学者在语言上的帮助[71],虽然这不是绝对正确的逻辑推理,但却导致了绝对的结果。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两者的圣经翻译十分相似,而当意见不同时,通常会倾向马礼逊译本,这从大英圣书会虽然曾经支持了马士曼的译经,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修订他的译本这一事实得到一些说明;而在马礼逊去世前不久,大英圣书会就开始了在马礼逊的监督下对他的圣经译本进行修订的工作。[72]
相反,浸礼会始终偏好马士曼译本,他翻译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被认为是胜过了所有其他译本。[73]根据浸礼宗的教义,水礼只可以浸礼的方式施行,并认为这是希腊文原文的唯一意义,这是浸礼会与其他宗派最本质的差异。和塞兰坡浸礼会所有语言的圣经译本一样,马士曼使用了“蘸”字,后来的译经者则采纳了“浸”字。今天浸礼会仍普遍使用后者的译名,出版与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圣经》。因与其他宗派在神学观念和专名翻译上的不妥协,浸礼会坚持不懈地对马士曼译本进行修订和翻译,由此产生了后来的高德译本、胡德迈译本、怜为仁译本。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白日升译本从未正式出版过,只是以手抄稿的形式孤独却不寂寞的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天主教传教士白日升未完成的圣经新约译本,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之间架起了圣经汉译的桥梁。因马礼逊和马士曼在翻译圣经时着重参考了他的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圣经汉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尤其在众多神学专名的翻译上,影响保存至今。这部福音合参本以“神”、“耶稣”、“罪”、“洗”、“耶稣基督”、“恩宠”、“先知”、“使徒”、“福音”等确定的专名,用“神”字翻译了“God”,而不是教皇圣谕的指定专名“天主”[74],通过二马译本在基督教中得以继承。即使在后来“译名问题”无休止的争论中[75],“神”字也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基督教《圣经》汉语译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这些专名译名的继承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如果没有白日升译本,在开拓众多其他传教事业的同时,马士曼、马礼逊仅在10余年里就能翻译和印刷圣经,这是不可想象的。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是基督教圣经汉译的集大成者,流传分布最广,中国基督教会至今使用。它是在基督教圣经翻译已有70年历史、多达30余种文言文、方言和白话文版本汉语圣经的基础上,各个宗派协作经历了29年才最终译成出版。圣经中译百余年来所历经的千辛万苦,尤其是涉及神学专名的选择和由此引起的争论,是教外人士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激烈,有些专名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真可谓“一名之立,百年踯躅”!
“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言语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76]王国维的名言讲述了在吸收引进新文化时,语言学方面的困难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时也是文化发展需要做出的突破。基督宗教四次入华都留下了圣经翻译的遗迹。唐朝景教的译经有明显的佛教语境和语汇,与今天的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相距很远[77]。元朝的译经至今没有发现文本文献,我们暂不置评。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文本和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只能与这种环境相调适。以“圣”、“经”来对应“神所默示的”基督宗教典籍,非常明显地昭示了他们的调适性传教策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力图通过这种方法使基督教的典籍与中国儒家和佛教的“经”处于同一位置。经过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们长期的本土化艰苦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能力都极大提高,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
通过对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如“亚伯拉罕”、“马利亚”、“摩西”、“保罗”、“所罗门”、“耶路撒冷”等等,奠定了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专名翻译的基础,奠定了基督教汉语神学系统的基础。
作为天主教最早的圣经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后来天主教思高译本的翻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专名在一定程度上被思高本圣经所继承,如“圣神”、“白冷”、“亚巴郎”、“撒罗满”、“若瑟”、“达味”、“若翰”、“梅瑟”、“先知”、“洗”、“耶稣基督”、“罪”、“福音”、“恩宠”等等。
神学家拉明·斯纳(Lamin Sennah)在讨论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基督教的本土语言性”及“福音的可译性”。对所进入文化的适应是基督教的特征,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进入希腊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并得以逐渐壮大,“皆福音的可译性使然”,它愿意、并且能够与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交往,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和努力下,成就了圣经中译事业。
附记:本文的部分资料收集得到了英国牛津中华基督教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美国圣经会、韩永生先生和李怀玉女士的资助和帮助,特此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06JJD73000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课题“圣经中译与近代中国”的阶段性成果。
[2]罗光:《利玛窦传》,台北,光启出版社1960年版,第168页。
[3]手抄稿开首空白页面上,手写以下英文:手抄本由霍治逊先生授命于1737年和1738年在广州誊抄,它已经过仔细校勘,毫无错漏。1739年9月呈赠斯隆爵士。
[4]《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大英图书馆亚非部藏,编号Solane MS#3599。
[5]截止1943年,《武加大译本》(Vulgate Version)是所有天主教圣经译本的钦定基础文本。
[6]为行文统一清楚,论文中的圣经篇名除原文引注外,均以和合本为准。
[7]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Chinese Researches (first printed in 1898, reprinted by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1966),p.96;G. W. Sheppard, “China and the Bible, Early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Lecture befor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on February 22,1929,”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No.17 (1929),p.398;A. J. Gam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4),p.13.
[8]Rev. Bernward H. Willeke, “The Chinese Bibl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No.7(1945),pp.450-453.
[9]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Macmillan,1929),p.190;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52;[英]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2页;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0]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威廉·克里创建,是欧美各国、也是英国基督教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对英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影响很大。
[11]Broomhall Marshall, The Bible in China,p.50.
[12]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p.45.
[13]当时大英博物馆包括今天的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
[14]大英圣书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又译英国圣书公会、大英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1804年成立于伦敦,是世界上最早专门推广圣经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圣经在东方的翻译出版,支持了基督教最早的两种圣经汉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曾在北京、上海、沈阳、张家口、天津、汉口、广州、哈尔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15]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是在威廉·克里影响下,于1795年在伦敦成立的跨宗派的传教组织,是基督教传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主要由英国的公理会、循道会、长老会和其他差会组成。
[16]LMS/BM, 30 July 1804,转引自苏精《来华之路:伦敦传教会的决定与马礼逊的准备》,《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9页。
[17]Testament可译为“约”,也可译为“遗嘱”、“遗命”、“遗诏”。早期圣经汉译均译为“遗诏”,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逐步改译为“约”。
[18]Eric M. North(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 (New York: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83.
[19]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1820),pp.89-93;Eliza A. 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39), Vol.1,pp.329-333.
[20]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2-11.
[21]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1924),p.118.
[22]BFBS Annual Reports 3 (1814-1815),转引自Thor Strandenaes,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 Ph.D. diss., Uppsala University,1987 (Uppsala:Almqvist,1987),p.45;Eliza A. 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3.
[23]LMS/CH/SC, 1.2.A., R. Morrison to ?, Macao, 18 January 1811.转引自苏精《来华之路:伦敦传教会的决定与马礼逊的准备》,《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第22页。
[24]LMS/CH/SC, 1.2.A., R.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Macao, no day November (1811).转引自苏精《来华之路:伦敦传教会的决定与马礼逊的准备》,《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第22页。
[25]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London:W. H. Allen & Co.,1883), Vol. 2,p.326.
[26]据称,1799年,马士曼曾到中国北方传教,待考。见王元深《圣道东来考》(写于1899年),香港《景风》总34期,1972年9月,第37页。作者王元深(1817-1914),中国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华人之一、基督教信义宗礼贤会牧师,外交家王宠惠的祖父。
[27]G.A. Grierson,“The Early Publications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aries,” The Indian Antiquary, 32 (1903),pp.241-254,转引自苏精《基督教中国传教事业第一次竞争》,《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33页。
[28]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Foochow:1868),p.9.
[29]BFBS Report 1807,p.154,转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p.46.
[30]《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牛津大学Regent’s Park学院安格斯图书馆(Angus Library)藏,有两本,索书号Chinese 2.27、Chinese 2.28。线装一册,56面,未具名出版地点、时间和译者。原文有句读。引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文同。
[31]国内最早的汉字活字印刷品为1822年的《华英字典》,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32]Joshua Marshman, 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 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Marshman to Dr. Ryland, Concerning the Chinese (Printed by J.G. Fuller, Kettering,1815),pp.16-17.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33]基督教和合本圣经是由美华圣经会、大英圣书公会和苏格兰圣经会支持、多个基督教宗派协作翻译而成的圣经译本,分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和白话本三种。1890年组成译经委员会,1906年出版深文理《新约全书》,1919年出版浅文理《圣经全书》和白话《圣经全书》,是中国圣经翻译史上影响最大的版本。中国基督教教会至今广泛使用的是其白话本,其他两种已经停止使用。截止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已印刷发行和合本达5000万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
[34]天主教思高本圣经是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籍神父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完整汉语圣经,也是中国天主教会唯一完整汉语圣经译本。它由1945年成立的思高圣经学会依据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圣经译出,1968年在香港首次出版。现被中国天主教会广泛使用。
[35]白日升译本的“四福音书”部分为圣经福音合参本,没有类似“约翰福音”等篇章的划分。为行文清楚,文中“约翰福音”由笔者加,此点下文同。原文无句读。
[36]《若翰所书之福音》,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9。共21章,72面,封面硬皮精装,铅字活版印刷,原为线装,后再用硬皮精装。封二用英文写道,约翰福音在塞兰坡被译为汉语,1813年塞兰坡教会印刷站出版。印刷质量上乘,纸质好,呈白色。原文有句读。
[37]和合本分“神版”和“上帝版”,故列之。
[38]马礼逊将白日升译本抄寄给马士曼,他在多封信中曾提及。见LMS/CH/SC, 1.1.1.C.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14 December 1809,转引自苏精《基督教中国传教事业第一次竞争》,《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37页。
[39]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3 April 1817. 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40]Joshua Marshman, 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 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Marshman to Dr. Ryland, Concerning the Chinese,pp.33-35;E.C. Bridgman,“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Chinese Repository, Vol.4,pp.253-255.
[41]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p.15.
[42]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2.
[43]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2-20,1890 (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0;许牧世:《中文圣经翻译简史》,香港《景风》第69期,1982年3月,第28页;简又文:《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44]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496-497.
[45]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 Appendix,p.50.
[46]白日升译本原文无14节。
[47]《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3,目录终尾处写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一十三年镌,木刻雕版印刷,线装小开本,双面印,纸质呈黄色。原文有句读。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大英圣书会、牛津大学亚非图书馆亦藏。
[48]马士曼的“新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12。线装,铅字活版印刷于塞兰坡,原文有句读。印刷质量上乘,纸质呈白色。美国圣经会亦藏,无索书号。
[49]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xii.
[50]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13 Dec.1816. 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51]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9 Jan.1817.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52]此列为马士曼的《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马可福音》)中的专名,个别专名在《约翰福音》中没有,为比较研究,故列出。
[53]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圣经新遗诏马太福音传》,咸丰二年宁波真神堂藏版,索书号TA1977.62/C1852;《圣经新遗诏全书》,咸丰三年宁波真神堂,索书号TA1977.5/C1853。
[54]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怜为仁(William Dean,1807-1895)译,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马太传福音书注释》,道光二十八年香港裙带地藏版,索书号Chinese 2.13;《圣书新遗诏》,咸丰二年镌,索书号Chinese 2.19;《创世传注释》,咸丰元年镌,索书号Chinese 2.3。
[55]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译,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新约传汇统》,同治六年宁波开明山藏版,索书号Chinese 2.23。
[56]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3 April 1817, Private published.
[57]书名为“Marshman’s Chinese Bible”,索书号mor.220.5951/B5m。
[58]Robert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Late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Compiled from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Deceased;to Which Are Added Occasional Remarks by Robert Morrison, D.D. (Malacca:Mission Press,1824),p.72.
[59]T. H. Darlow, H. F. Moule, History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03),Vol.1,p.184.
[60]书名为《旧遗诏书第一章》,“依本言译出”,共3页,有马礼逊英文笔迹,注明181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索书号TA 1977.2/C1814。原文无句读。
[61]《神天圣书:旧遗诏书》,1827年吗喇甲印刷,英华书院藏版,线装,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无索书号。原文有句读。美国圣经会、大英圣书会、牛津大学亚非研究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亦藏。
[62]马士曼的“旧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11、Chinese 2.12、Chinese 2.5,线装,再用棕黑色底红蓝色花纹硬皮重新精装。原文有句读。美国圣经会亦藏。
[63]苏精:《基督教中国传教事业第一次竞争》,《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31-152页。
[64]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407.
[65]LMS/CH/SC,1.4.B. 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 Macao,5 July 1815.转引自苏精《基督教中国传教事业第一次竞争》,《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41页。
[66]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F. 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 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此主题的研究论文见马敏《语法书:马希曼是否抄袭马礼逊?——19世纪初早期英国传教士之间的一场争论》,陶飞亚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版。
[67]Joshua Marshman, Letter to F. 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
[68]谭树林:《<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亦见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69]A. C. Moule,“A Manuscript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5 (1949),pp.30-31.
[70]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1]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2-20,1980,p.50;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第6页。
[72]Thor Strandenales,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pp.23-26.
[73]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844,p.36.转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p.53.
[74]1704年,教皇克勉十一世谕旨只能用“天主”、不能用其他来称呼造物主。见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p.422;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1-232页。
[75]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圣经的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6]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
[77]限于文章篇幅,仅举几个译名为例:瑜罕难(景教)、若翰(天主教)、约翰(基督教);卢伽(景教)、路加(天主教、基督教);摩矩辞(景教)、马尔谷(天主教)、马可(基督教);明泰(景教)、玛窦(天主教)、马太(基督教);弥施珂(景教)、默西亚(天主教)、弥赛亚(基督教);移鼠(景教)、耶稣(天主教、基督教);天尊(景教)、天主(天主教)、神/上帝(基督教);阿罗诃(景教)、雅威(天主教)、耶和华(基督教);浑元经(景教)、创世纪(天主教、基督教);传化经(景教)、宗徒大事录(天主教)、使徒行传(基督教);牟世法王经(景教)、梅瑟五书(天主教)、摩西五经(基督教);宝路法王经(景教)、保禄书信(天主教)、保罗书信(基督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1.来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
永久域名:iwr.cass.cnE-Mail:zjxsw@cass.org.cn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京ICP备0507273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