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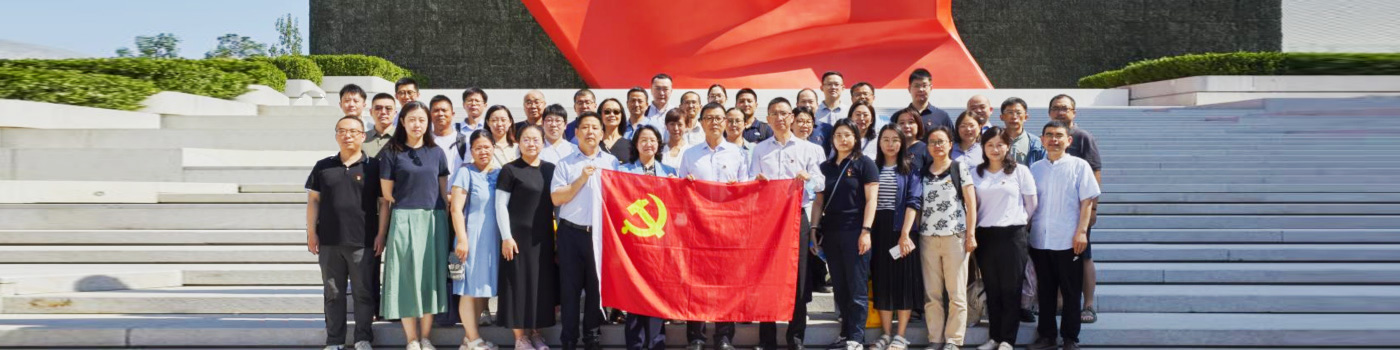
“天方学人”王岱舆(约1570-1660)、马注(1640-1711),明末清初回族穆斯林学者,学通“四教”(儒释道伊),他们撰写《正教真诠》、《清真指南》等著作,以汉语言文字和中国传统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开始构建中国伊斯兰教义学。本文主要以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问答记言》和马注的《清真指南·客问》的相关材料为依据,来讨论明清之际回族穆斯林学者的文化自觉及其回儒对话活动。王岱舆、马注等人的上述学术工作,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回回民族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回儒”之间的一次学术对话。本文的所谓回儒对话,“回”指伊斯兰文化,“儒”则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和特色的、包括释道在内的、尚未融合伊斯兰文化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是这个民族得以在文化上自立的基础;文化自觉,更应该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回儒之间的这次对话,既有利于双方在学术思想层面的交流和沟通,又成为回回民族在学术思想层面融入“中华民族”的标志,同时也确立了回回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学术地位。当然,这场对话尚未成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对话,而是基于伊斯兰教立场的一次单向度、封闭式的宗教学术对话。
1、予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而已
岱舆王子[3]《正教真诠》书成,教内学者读后有三个疑问,作者对此一一回答,这些内容都记录在《正教真诠·问答记言》[4]里。通过这三问三答,我们可以约略把握作者著述的“区区苦心”。
第一问,“子之书将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诸家,彼此辩论,不几树敌乎?”“但言清真之道”可也,这是大多数学人的治学态度,民族文化建设是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因为文化辩论并不就是文化建设。
岱舆先贤谓:“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既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发缨冠而救,非木石则奸顽人也。”(《正教真诠·问答记言》)作者对此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首先,护教卫道的文化立场。从伊斯兰教立场出发,认为清真教道乃人道当然。今天我们所应注意的并非是其卫道之立场,而应该注意其所卫之道的具体内容:即“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他认为这就是“正学”。而自伊斯兰教义学形成以来,“命人行好,止人干歹”就一直是其基本内容之一。其次,刚毅弘道的文化精神。对于上述“正学”或“教道”,如知而不言,或言而“不能恺切诚恳”,都是作者认为所不可取的。知道,就应该传道,具备这种精神应该说是一个热爱道(正学)的学人。再次,消弭冲突的文明对话意识。历史上回儒之间基于文化隔阂的现实冲突,譬如“操戈同室”,有良知的中国学人都应该“披发缨冠而救”。通过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来消弭一般的民间冲突与社会纷争,从文化层面来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学者作为社会公众知识分子(公众代言人),所应该具有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
第二问,“儒者之道博大渊微,至于性理尤宋贤精粹之所在,子所引论,特其浮浅糟粕耳。其微,子固未深求也。”这种观点(精粹与糟粕之分)总而言之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具体针对性,所以难免大而无当之讥。岱舆先贤就此问阐述道:“天下事有不齐,理无二是。予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而已。夫国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长,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纷纷以理气二字尽之,是天下国家可以无君长而治也。予辩其异吾道者而已,不暇计其浅深也,浅者异则愈深愈异也。若夫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与吾同者,予焉敢妄议其是非哉!”
就是说,作为万物外在形式的“事”可以千差万别不等,但是作为万物内在根据的“理”则是一致的。国有君主,家有户主,大千世界也应该有一个主宰,这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宇宙万物存在一个主宰,而宋明儒家学者大多认为“理”或“气”是世界的本原。果然如此的话,那么就会得出国家无君主、家长也可以得到治理的荒谬[5]结论。在此,岱舆先贤基于伊斯兰文明的视角,给出了一个文明批评或文明对话的第一条学术准则:别同异,即“不计人我,但论同异”。必须说明的是,岱舆先贤所谓的“别同异”这一中国伊斯兰学术批评准则,并非是一般习见的党同伐异的政治原则,也不是“以己之是非为是非”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本位原则:党同伐异基于现实的政治立场,文化本位原则是以某一具体文化为本位来区别同异,可以说是基于本位文化立场的“党同伐异”。笔者看来,岱舆先贤所谓的“别同异”,是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此处的“同”是指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基本教义和中国传统思想之同,此同属于理性分析的结果,这是运用中国传统思想基本准则而进行的理性分析。比如对于最为基本的世界是否有神以及“认主独一”问题,一方面从国有君、家有长的常识层面来论证世界有主(神);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传统的“过犹不及”思想来证明“太过则堕于空无,不及则狃于形气”(《正教真诠·正教》),就是说以物质性的气为世界主宰(本原)未免“不及”,而以空无为宗则又太“过”,以此来肯定“一神论”的真理性。
关于宋儒之得失,清初回族穆斯林学者马注(1640-1711)指出,“徒以语言文字之所及则及之,语言文字之所不及则不及之。”(《清真指南》卷二,“客问”)就是说,自宗教神学层面来看,宋儒较先秦已经大为衰落,自先秦至宋中国传统文化在逐步“去宗教化”[6]。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逐步“去宗教化”的过程,[7]应该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不拟涉及。而这种不断地“去宗教化”的趋势,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这也正好是与伊斯兰文化相异之处。一个是稳定的宗教文化,一个是不断地“去宗教化”的人文传统,宋儒正是这一人文精神的自然延续,二者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正好迎面相撞。宇宙万物均由真主安拉造化,这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首要基础;而宋儒纷纷以“理”、“气”为世界的本原,自然要遭到穆斯林学者的批评。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并非完全基于伊斯兰教立场,也是自先秦儒学传统来批评宋儒对于先秦宗教神学传统的“背离”。马注认为,先秦的中国传统思想“然犹仿佛清真,惟事上帝。”而后来“玄门谓上帝乃海外光严妙药王之子(宋真宗祥符七年以功德封玉皇上帝),释教谓光严药王佛乃释迦弟子,其与《诗》之‘上帝临汝’,《书》之‘昭事上帝’,名同而实异耶。”(《清真指南》卷二“客问”)就是说,《诗经》指出,“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荡荡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这是明确肯定上帝的存在,并强调上帝可以接近人类,对于上帝我们要“无贰尔心”并“小心翼翼”地“昭事”。《尚书》谓“上帝不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也是肯定上帝具有福善祸恶的能力。至于秦汉以来文化传统(包括儒释道)里的上帝,与先秦之上帝已经是“名同而实异”了。
今天也有学者认为,古代夏商周存在人格神的信仰,或者“准人格神信仰”,而孔子对三代人格神信仰的保留,主要存在于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春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所建立的经学传统中保留了人格神的信仰,而后儒的心性化义理化倾向则淡化了人格神的信仰”[8],也就是说,孔子对于天的理解主要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具有人格的天,如《春秋》肯定上帝(天)的震怒降灾,《书》宣讲上帝(天)的福善祸恶,《诗》强调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这就是春秋时期对于殷商时期具有人格神特征的自然宗教精神的继承。至于《大学》、《中庸》、《孟子》,天被侧重理解为心性的、义理的天,开始向人文教化转变,即由以人格神信仰为特征的自然宗教向以人文精神为特征、以神道设教为宗旨的文化宗教[9]转变。宋儒将天与心性良知等同,此天明显属于文化意义的天,而非宗教神学意义的天。因此,笔者以为岱舆先贤的“别同异”并非完全站在伊斯兰立场,而是兼有殷商至春秋时期的侧重人格神的文化传统。其实,这种“不计人我,但论同异”的文化批评准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固有资源。如汉高祖时的儒生陆贾就认为,“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虽然身为“汉代重儒”第一人,陆贾却提出“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精神特质的体现。这种文化精神特质因其胸怀之博大、视野之开阔而具有久远的魅力,应该说具有世界一体和人类一家的文化自觉意识。
第三问:“子既深论二氏,乃子之书中多引用二氏之语,几于入宗入玄,何也?”岱舆先贤回答说:“清真之经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也。予特著论以彼达此,悉属借用,顾其理何如耳,其词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为异乎?”
当时有学者问道:您既然对于释道二氏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而您的著作中对于释道二氏的话语又多所引用,几乎等同于释道学者,这是为什么?岱舆先贤回答说:伊斯兰教经典很多,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教外(汉语)学者对此多不甚了了。为了阐述伊斯兰教义,我特地使用汉文著述。语言文字均属于借用,旨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汉语表达方式本来就是借用,所以也并不排斥释道二氏的语言概念。
就是说,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概念则是表达思想的材料,这些都是一个特定思想内容具体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使用汉语言文字与概念的目的,就是“以彼达此”。在此,我们再次看到王岱舆作为学者的严谨求实精神和文化开放心态,为了沟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与概念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平等的,没有此疆彼界。为了实现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与概念的藩篱,转换素所习惯的话语表达方式。王岱舆所进行的文化对话,主观上固然是为阐述伊斯兰教思想内容,客观上则是通过汉语言文字与概念等表达方式的借用而把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特质输入伊斯兰教,使其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随着“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数量的增加,汉语言文字概念(如清真、真主、先知、经训、五功、前定等)的大量涌现和逐步成为伊斯兰教的专有名词,伊斯兰教开始在思想和理论上走向本土化和地方化,由所谓“在中国”而至于“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系统的理论创造和整体的转化过程就开始于明清之际的系列汉文译著活动,而包括唐宋以来的伊斯兰教汉文石刻、碑铭、楹联等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理论创造与转化过程的发端。似乎可以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首先是来华和在华长期居住的穆斯林“身份”的转变(由外来番客之侨民转变为以中原为家的主人),即实现所谓人的“华化”[10],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华化,即转化为“中国穆斯林”,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清真寺建筑形制与信仰表达方式,无不带有中国特色;其次,才是宗教教义的“中国化”,以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出现为系统转化标志。这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总体特征是相吻合的,即作为穆斯林身份的个人来到中国在先,而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则是其相伴随的现象,并且伊斯兰教长期局限于穆斯林内部传播(新疆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
2、人生之本,莫重于亲,莫尊于主
马注在其著作《清真指南·客问》[11]十六答里,列举了多达16个问题,并一一回答,以此来沟通回儒两大文化传统。16个问题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清真何始”、“真主无像,不落声闻,尊经自何而有”、“然则真主可见欤”等3个问题,属于伊斯兰教本体论范畴。第二组包括“不事天地而事真主,何也,敢问天地人物之所从生”、“何谓无始无终”等4个问题,属于认一论范畴。第三组包括“然则二氏之教非乎”、“二氏既非正教,儒者之道何如”以及“古今既出一体,何为回汉各别而教理不同者,何也”等问题,属于自伊斯兰立场进行的又一次回儒[12]对话。这一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单项度对话,对话者主观上在于阐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思想,客观上则增进了回儒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文化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特质自由地进入伊斯兰文化,成为构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分别加以阐释,以探索马注的文化对话思想脉络。
首先,第一组对话以伊斯兰教信仰对象真主为核心展开,第一问是问清真教(伊斯兰教)如何发端?马注答以“始于天房,天房之教,始于人祖阿丹。”这一回答包括阿拉伯地理知识、伊斯兰教知识和伊斯兰教传说。第二问是针对真主无像而问“天经”自何而有,答曰:“天仙在天,圣人住世。传之者天仙,受之者圣人。”即以天仙来沟通真主与先知(圣人),天经(即《古兰经》)由天仙传达给先知穆罕默德。第三问:“然则,真主可见欤?”直接询问这一最为核心的问题,真主无像,又有“天启”传达给作为人的先知,既然无形那么如何可见(可以信仰),对于儒家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马注将问题转化为“见己身之性灵,则可以见真主矣。”即用传统儒家思想概念“性灵”之可见与难见(犹如不可见)来譬喻真主之可见与难见,于是引出“性灵安在”问题。至此,马注成功地将一个在儒家学者看来十分陌生的神学命题(真主是否可见)转化为一个儒家语境里的哲学命题(性灵安在),并熟练地使用儒家话语概念来加以阐释道,“君之欲动、欲静、欲语、欲默,皆性灵之用。至其本体,则放弥六合,退守寸衷。”即人们的动静语默皆性灵之用,而性灵之体则“放弥六合,退守寸衷”。就是说,由性灵的体用我们可以“感知”而不可以“见知”,这是儒家学者所熟悉的话语和言说方式,被认为是精细和高深的学问,而在穆斯林学者看来则属于小神秘,充其量不过是哲学认识论上的神秘。至于真主的无像与无处不在,在儒家学者看来则是粗糙的和肤浅的甚至是十分矛盾的表述,而在穆斯林学者看来则是超越理性(理性之后)的大神秘,属于神学信仰层面的神秘。
马注认为,性灵之体譬如“月印千江,同而不在;风来枕席,摸之则无。此一身之主尚不可见,而欲见造化性灵之主乎?”在此,马注以性灵之不可见(难见)来说明“造化性灵之主”的不可见(难以见知),可以说是以此达彼,加以融会贯通,阐述真主作为造物主的不可见(即不可以见知)。但是我们如何来认识真主的存在呢?认主凭据之一,马注指出“夫天覆而地载,日升而月沉,阴卷而阳舒,春荣而秋实,万物消长,亘古如一,此皆真主之大能,分明认主之凭据。”即天高地卑、日月周旋、阴阳变化、春华秋实等自然变化均遵循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真主大能的显现,也是真主存在的凭据。比如“楼阁池台,建者必有其人,若以楼阁池台即为所建之主人,则误矣。”这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变化遵循一定规律来证明真主的存在。认主凭据之二,马注指出“身体发肤,成于父母而养于天地,其夭寿穷通,男女贵贱,谁使之然钦?在胞饮血,出腹啖乳,五官灵明,百骸任役,似此至妙安排,或亲或己,兴废权衡,渺茫莫测,此皆真主之妙用,分明认主之确据。”如果说天地日月之变化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于遥远,那么个人的男女贵贱、夭寿穷通、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的精确规定与巧妙安排则痛痒攸关,而马注认为这些都是真主所安排的,也都是真主存在(即认主)的证据。马注指出,人好比“丹青文理,画作必有其人,若以贮积丹青文理者即为画作之工人,是又误矣。”就是说,大自然好比一座房子,人比如一幅画,房子本身不能制造房子,颜料只是绘画原料而不是画家,到底谁才是这个房子(大自然)和这幅画(人类)的创造者呢?马注指出,“在老曰道,在释曰佛,在孔曰儒,各是其是,逐教称尊,互相争论,无有宁波。”在此马注是把三教从文化视野和教化功能方面加以并列,而忽略作为文化传统的儒与宗教传统的释道之别,意在强调三教形成“各是其是,逐教称尊”的局面。他认为,这就如同“世乱民危,国无共主,有识者决不以一方之尊而当天下之至尊也。”三教各有所尊,但不可以一方之尊而为天下之至尊。至于伊斯兰教所崇拜的,则是“宰乎天地万物之主”。就是说,伊斯兰教所崇拜的只是主宰(造化)天地万物的真主,至于祖述周礼以文王为宗的儒者、以无为自然为宗的道、以及觉悟的圣哲佛祖均非天地的造化者。
其次,第二组问题属于伊斯兰教认一论(认主学,即宗教哲学)范畴。第一问即是为何“不事天地而事真主”,马注首先指出,自然界与人类都是真主所造化,“日月星辰,火风水土,本于太极;太极之初,本于无极;推无极之始,乃天地之所从生也。天地既有从生,是知天地非自有。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坏,长静不动”。就是说,天地万物均非自在,都有毁坏之日,所以都是派生的。其次,马注区分存在为三类,“无始无终者,乃真主独一之有;有始无终者,乃天仙人神[13]之有;有始有终者,乃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有。”第一类为真主独一无二的存在,是永恒的;第二类为真主所造化的具有灵慧之命的天仙人神的存在,有始而无终;第三类为低于人类的动植矿物的存在,有始有终。马注指出,动物“不能察识物理,分别善恶,至死而生觉之性随灭,不能与天仙人神同久。缘其无灵慧之命,所以有驱杀禽兽之理,而无赏罚禽兽之条。草木金石有生长而无知觉,感四行之变蒸,根本若死,生性随灭。”植物仅具有生长之性(生性),动物兼有生长之性和知觉之性(觉性),但无灵慧之命,身死而生觉之性即消失。“设以生长之性同于知觉,知觉之性同于灵慧,灵慧之性同于真主,何异二氏空无,万殊一体?且其六道同根,轮回生死,妄议猜度,自误误人。”马注认为,如果混一生长、知觉、灵慧三性及其与真主之间的差别,就会等同于强调万物一体与空无的二氏(释道),释氏的六道轮回之说即以此混一为基础,所以属于“妄议猜度”。
第三组问题,旨在讨论回儒两大文化传统的异同,属于回儒文化之间的再次单向度对话。第一问,“二氏之教非乎?”问题开门见山,直截了当。马注委婉地将话题转化,谓“二氏之教,古之所谓杨墨也。杨墨之道,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就是说,二氏(释道)之教犹如古代所谓的杨墨: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14]“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所谓过犹不及,杨墨之道不讲五伦关系,所以会形成“虎狼一体,蛇蝎不伤”的无差别局面。他认为,欲通过二氏“转人之死生祸福,智亦陋矣”;今人不知崇拜独一至尊的真主,“乃知见有以限之也”。间接地否定了二氏的真理性。
第二问,更径问“儒者之道何如?”这一问,引发马注纵论儒道、释道和宋儒。首先,马注认为儒道之所以独隆于东土的原因是,“宇宙间纲常伦彝、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道,理尽义极,无复漏遗,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非此则人道不全,治法不备。”就是说人世间修齐治平之道,儒者所说可谓“理尽义极,至中至正,不偏不倚”但是儒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人生之理,生前谓之始,现在谓之中,死去谓之卒。儒者第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观之士,不能无疑焉。”又“始之所以来,终之所以往,造化本原,生死关头,一切不言。”就是说,全部人生包括生前(始)、现在(中)、死后(卒)三个阶段,儒者只讨论现在(中)阶段,而拒绝讨论生前、死后两个阶段(即缺乏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那些好学深思者自然会有疑问。马注指出,“人生之本,莫重于亲,莫尊于主。”即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尊亲”和“认主”。其次,关于释道,马注指出“释氏之弃父母而不养,舍身喂虎,割肉啖鹰”,这种人生态度(生命观)“与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之说大相矛盾。”他认为,这种生命观(人生态度)不仅是“邪说诬民”,而且简直就是“率兽食人”。再次,关于宋儒,马注认为“宋儒起而阐明至道……惜其未得真主之明命,至圣人之真传,徒以语言文字之所及则及之,语言文字之所不及,则不及之。”即宋儒对于至道的阐释,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本身与表面,语言文字不能达到的则不予涉及。
第三问,“古今既出一体,何为回汉各别而教理不同者”,马注认为原因在于,“开辟之后,人生日繁,教道四达,流被日远,认理或殊,向背各异”。即他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中心向边缘不断传播(也是个逐步衰退的)的过程,传统儒学虽然“不无见闻失实,然犹仿佛清真,惟事上帝。”即虽然在文化传播和转化过程中会有信息溢出(流失),不过人们依稀记得要“惟事上帝”。但是“自玄释之论出,而上帝又不可考矣”,如此人们开始“事佛,事仙,事神事鬼,各拟臆见,使海内之士虽有才智,悉入牢笼”。就是说马注认为,佛教的传入,扰乱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局面。
3、结语
岱舆先贤的对话立场与对话视野较为开阔,“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这一对话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对话,摆脱门户之见;马注则是自穆斯林学者的立场出发,针对传统儒学、二氏(释道)和宋儒展开了具体的讨论,一面吸收儒家思想,一面弘扬伊斯兰文化,在具体对话论点上,即如何寻找跨文化对话的最为恰当的话语,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总之,单向度、封闭性的宗教学术对话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虽可准确保存某一宗教文化的基本思想,但对于其他文化传统的讨论难免失之偏颇,因此难以形成跨越文化壁垒的深层学术对话局面。
注释:
[1]石河子大学特聘教授。
[2]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项目批准号:04JZD0005)的阶段性成果。本论文曾在“南京大学��哈佛燕京文明对话论坛·2006昆明会议: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会议上宣读,并被收入《“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称岱舆王子,既是因袭传统,也顺便表达对于传统学人的尊敬之心,如岱舆先贤然,其外无他矣。
[4]以下所引《正教真诠》原文,均出自王岱舆《正教真诠·问答记言》,所使用版本系王岱舆著、余振贵标点:《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在封建社会,人们不能设想没有君主(皇帝)的国家生活,认为那是非常荒谬的。当然,君主也可以理解为国家领导人、政治领袖。
[6]有学者谓,“到了宋代,朱熹等理学家们进一步吸收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冯今源:《试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渗透》,《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7]从子产(?--前522)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至孔子(前551-前479)的“敬鬼神而远之”(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再到荀子(约前325-约前235)的“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一方面固然是人文精神的彰显,另一方面也是儒学“去宗教化”的高潮。
[8]蒋庆:《追求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问题》,2002年6月范必萱根据录音整理。资料来源:http://www.confucius2000.com
[9]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宗教,就是以人文精神为特征、以神道设教为宗旨的一种终极关怀模式,其中文化传统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宗教神学则退居次要与边缘地位。也有学者指出儒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而不是神学宗教(蒙培元语)。
[10]关于元代西域人的华化问题,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析论甚详。
[11]马注:《清真指南》卷二“客问”。以下所引马注观点均出自卷二“客问”,不再一一注明。
[12]此处的回是指伊斯兰文化,儒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和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13]此处的神指天使,为真主造化,并受真主的差遣,完成各种工作。
[14]原文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博客,引自博联社网)
1.来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