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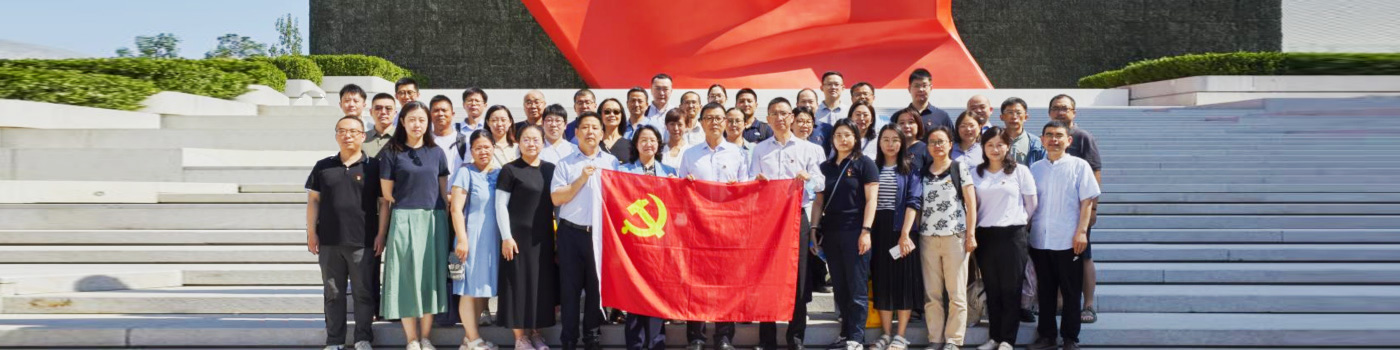
任何一种宗教都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宗教多样化已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宗教间的关系也成为各国都要处理好的几大社会关系之一。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多元宗教共处的情形尤为显著,其宗教界与学术界也不断探索建立宗教间互尊互信关系的模式与路径。结合英国的宗教多样化现状,了解英国宗教学界推动的“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运动,对中国建设和谐宗教关系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英国宗教的多样化现状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是最早进入全球舞台的国家之一,因此全球化在宗教上的表现,如多元宗教共聚的现象,在英国十分明显。英国的宗教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世俗化程度较高,传统的主流宗教严重衰落,外来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发展呈上升趋势。英国是欧洲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宗教持消极态度的人在发达国家中排在前列。即使在那些声称信仰上帝的人当中,大多数不加入教会,也不参与宗教活动,不足10%的人参加经常性的礼拜活动。在圣公会与天主教等传统主流宗教中,神职人员数量不足,老龄化现象严重。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对宗教也较为警惕,反对公立学校以宗教作为入学标准,反对教师招聘中的宗教要求。甚至直接要求教会服从国家世俗法律,不得以教会传统为由歧视女性等群体担任圣职。总体而言,以圣公会为代表的基督教主流派别在英国的衰落是较为严重的。与此相反,由于英国较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从英国前殖民地如印度、巴基斯坦及非洲等国进入英国的人口增长迅速,导致上述族群的传统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灵恩派基督教快速发展,英国宗教版图变得更为多样化和碎片化。
2.圣公会在英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虽然总体而言,圣公会的衰落较为严重,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圣公会在英国没什么影响力。首先,作为英国的国教,圣公会以及其所植根的基督教传统长期得到英国社会的支持,其根基非常扎实,文化底蕴深厚,国人价值观长期受其浸染。基督教在学术界和文化界都有较广泛的基础,其发出的声音也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圣公会延续了罗马公教的教区制,在体制和人员上都有一个整齐而严密的系统,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在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由于宗教与族群的多样化、社会的世俗化,圣公会的这一体制不甚显著。但深入到乡村或小城镇,教区制在整合英国地方社会方面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最后,圣公会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借助于英联邦这一体制,它在国际宗教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在英联邦国家的传播,圣公会拥有6千万信众,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其精神领袖,是仅次于罗马公教的基督教派别。国际圣公会体制,与政治上的英联邦(Commonwealth)一道,是英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渠道。
3.伊斯兰教在英国公共社会领域内的角色日渐显著,成为英国宗教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劳工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巴基斯坦、海湾国家的长期殖民历史,穆斯林得以大量涌入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与基督教等传统宗教在英国走向衰落不同,由于伊斯兰教对信徒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和规范,宗教与族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穆斯林社区在英国常常以整体的方式较独立地存在,与英国世俗化的社会构成一定的张力。而且,作为少数族裔的社区,为了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穆斯林的宗教认同感更加强烈。在一些极端事件如拉什迪事件、“9·11”事件、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等的渲染之下,伊斯兰教与英国社会形成较为紧张的关系,与代表英国主流社会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也被人们从“宗教或文明冲突”的角度加以打量。
综上所述,英国的宗教多样性有两个基本的要素,即基督教仍然充当某种形式的主体,而伊斯兰教的兴起则是最显著的现象。因此,如何建构和谐的宗教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构成英国政界、学界和教界都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对话”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以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为例,他认为“对话”是“对他人严肃性的认可”,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进行其他深层次合作的起点。他本人亦广泛地与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如天主教教宗、信义宗联盟、印度教和犹太教领袖等进行对话。在学术界,作为英国“国学”重镇的剑桥大学神学系设立“跨信仰项目”(Inter Faith Program),尤其是其核心人物大卫·福特(David Ford)创造性地提出“经文辩读”运动,即基于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具有共同的经典渊源之事实,通过不同信仰群体阅读、讨论彼此的经典,来实现信仰间的理解与对话,进而由此重思宗教在社会中的公共角色、宗教学研究的可能路径等。其思路与实践对于具有多元宗教文化背景、试图厘定宗教与公共社会之关系的中国宗教学界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二、以“经文辩读”推动宗教对话:剑桥大学的实践
在宗教多样化的背景之下,英国宗教界和学术界尝试过多种宗教对话的模式。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社会实践派”,其基本思路就是认为各大宗教应该将各自的教义主张、理论差异先搁置一旁,以“苦难的世界”作为实践的对象,在携手解决社会面临的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合作。这种对话之路确实是对各大宗教“济世爱人”理念的实践,使宗教界在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中增进了友谊,但是,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它回避了宗教作为一套知性体系、意义系统的性质。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提供一套解释世界、人生的意义系统。信仰者总是希望通过理论学习或社会实践来加深他们对这一套意义的理解深度,如果宗教对话或合作不能为参与者们提供深化理解的可能,它的吸引力将大为降低,也难以具有持久的动力。其次,社会实践领域固然重要,但对于各大宗教来说,仍属派生性或边缘性的领域,其效果不能对整个信仰群体产生广泛的作用,影响有限。再次,在社会实践中将教义或理论悬置起来,实际上偏离或模糊了宗教对话的目的,参与者对另一种宗教的理解没能深化,宗教对话所追求的目标,即信仰上真诚尊重、相互借鉴、在跨越边界中进行深度学习等,成为不可企及的奢望。
事实上,剑桥大学“经文辩读”运动的创始人大卫·福特在发起该运动之前,就曾在伯明翰地区从事过跨信仰的社会福利工作,例如,来自于不同宗教的人士共同致力于把一些旧房子翻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寄宿等。他个人曾言,虽然他从事这一工作达10年之久,但从中却很少感到“知性的吸引力”。在加入剑桥大学神学系后,他受到犹太教学者通过细读《希伯来圣经》来应对现代性、反思大屠杀之后的犹太处境的启发,开始倡导以“回到经典”和“经典的交叉阅读”为理念的“经文辩读”运动,来进行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人文主义甚至与无神论之间,尤其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之间的宗教对话。笔者年初在剑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参加该协会举行的数次“经文辩读”研讨,在此对这种宗教对话模式的操作方式做一介绍,并从理念上对其进行分析。
从操作层面来看,“经文辩读”并不复杂。它从各大宗教的本根即权威经典开始,把它开放给其他宗教传统的人士来阅读和解释。它采取的形式是“小组读书班”,即由不同宗教的代表组成,他们被称为“辩读者”(reasoner),可以是学者、宗教界或政界人士。大学是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但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如医院、教育或文化中心亦未尝不可。每次都围绕某个主题,如创世、信仰、正义、宽恕、债务、暴力、女性等,从亚伯拉罕系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抽取短小的经文。有时,一些后世评注的文本也可以作为补充,如《塔木德》、基督教教父著作、《圣训》等。辩读者可以依据自己不同的传统或解释,来阐述自己对于这些经文的理解。
对这些文本的辩读,通常由一个简短的导读开始。理想的导读是来自某个宗教传统内部的人,但并不局限于他们。例如,在进行“创世”的辩读时,《创世记》由一个犹太学者来介绍,《约翰福音》则由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介绍,《古兰经》篇章则由伊斯兰教学者介绍。每一次“经文辩读”的时间大概为两个小时。一般来说,在导读阶段不应做太多延伸,否则它就成了一个讲演,而不是对话。通过这样的互读,参与者就能知道其他传统的人如何理解它,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传统的角度发表评论。在辩读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对某一传统的看法表示认同,而分歧也经常出现。它使人深刻地看到一段经文所可能具有的多样内涵,以及经文中的只言片语如何在不同传统中被衍生出丰富的内涵。在这样的阅读实践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对经文会形成开放的态度,拒绝自己也拒绝他人独占对经文的解释。在某次辩读的最后,人们也无需得出某个共识,结论始终是开放的。
在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后面,实际上蕴含“经文辩读”的发起者们通过经典互读的方式,来推动宗教间对话的基本理念:
“经文辩读”是多样的宗教信仰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真诚沟通的活动。在对话中,每一宗教传统都被真诚地对待,是被尊重的“另一个”。
“经文辩读”并不是要消解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异,而是在对差异的尊重之上,寻找深化理解、丰富自身的因素。
“经文辩读”既注重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又强调当下的处境,在对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的回应中重归经典,这样才能使经典互读的成果具有当代相关性。
“经文辩读”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作为邻居的其他宗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最终使宗教对话成为一种对更高智慧的寻求。
“经文辩读”的实践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自我反省,包含着对于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自我独断的消解。
在文化史上,权威经文的阅读与解释一直是宗教传承和发展的核心。而“经文辩读”运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宗教传统中最核心最神圣的经典开放给别的宗教,邀请他们对经文进行阅读和解释。就此而言,它是对宗教多样性、对宗教“他者”的深度认可。
三、“经文辩读”与中国的和谐宗教建设
目前,“经文辩读”主要是在英美学术界和宗教界开展,也得到西方社会穆斯林的热烈回应,同时它也积极走向伊斯兰核心文化圈(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学者对话的两次“经文辩读”会议,分别在兰贝斯宫和多哈举办)。但作为一种宗教对话的新模式,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也不难操作,因此对于中国的和谐宗教建设也有相当的启发之处。
首先,它不是将宗教对话局限在边缘性的伦理教导或社会实践方面,而是集中到各大宗教的核心经典。宗教经典在各大宗教传统中享有权威地位,是各宗教之理论和实践的源泉,就此而言,阅读彼此的宗教经典既是底层的工作,因为经典是各大宗教的根基;又是顶层的工作,因为阅读经典、解释经典而形成的理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广度而言,“经文辩读”的对话成果将影响到各大宗教的最广泛信众;从深度而言,从另一个宗教传统的角度对经典所做的诠释将使双方都发生深刻的改变。
其次,它通过以比较促沟通,以互读求理解,赋予“和而不同”以新的内涵。按“经文辩读”创始人之一的大卫·福特所言,通过不同宗教经典之间的互读,人们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提升差异的品质”。也就是说,人们不只是知道彼此间是不同的,而是通过对彼此权威经典的阅读,从本根处知道差异到底在哪里,知道差异的由来,同时知道差异的走向。这样,不同宗教在共处时,就不会仅仅以面具化的“我们”与“他们”进行简单区分,而是在彼此深入了解基础上的“美美与共”。
最后,它鼓励人们进入另一种传统的深处,在对其他宗教的深度学习中发展出友谊与尊敬。要深入了解蕴含在经文后面的深厚传统,需要经历多年的学习与积累方有可能。因此,以经典互读作为宗教间对话的形式,有助于信仰群体之间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经文辩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和社会的实践,使人们在年复一年的学习中,深化对自身传统、其他传统以及当下社会情境的理解。这样,“经文辩读”既避免了空洞的理论玄谈,又戒除人们急于达成某种共识的急躁心理,在从容的深度学习中,人与人自然会发展出友谊与和谐,作为理论成果的跨宗教文本诠释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宗教文化土壤比西方文化具有更大的先天优势,更切实可行,而且更能产生有普世意义的对话成果。第一,在中国佛、道教中,经典互读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它们不仅互注经典,而且很多经典都是共同被佛道教所尊崇。将中国本土宗教之间经典互读的传统揭示出来,对当今世界处理宗教间关系有着广泛的启示,是对当今文明对话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第二,在外来宗教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典互读也是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路径。形成于我国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回儒”所采取的“以儒诠回、回儒共明”策略,就是在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之间的经典互读。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此后产生的一批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也开辟了一条用儒家经典来诠释天主教信仰的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的中国经典被援引来论证天主教的信仰。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典互读中,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创造性的丰富,发展出某种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把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两种“亚伯拉罕宗教”与中国宗教之间的经典互读互释的个案整理出来,将对世界的和谐宗教建设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第三,在当代中国,鼓励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深入地阅读中国经典如《老子》、《论语》与《孟子》等,用中国经典来诠解《圣经》或《古兰经》,或者反过来用伊斯兰教或基督宗教神学来诠释中国经典,是它们在神学思想上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途径,也必将从根本上有益于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经文辩读”运动对大学在宗教间对话中的角色之重视,也可为中国和谐宗教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大学不从属于任何宗教,但它可以成为各宗教进行对话、构建和谐宗教的“学术中间地带”。这样的理解,同样适用于对大学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宗教中角色的定位。如中央民族大学设立的“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研究基地,就是希望借鉴剑桥大学“经文辩读”的有益经验,通过经典互读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国构建和谐宗教关系、发挥宗教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探索性实验。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12年第5期,引自中国宗教网)
1.来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