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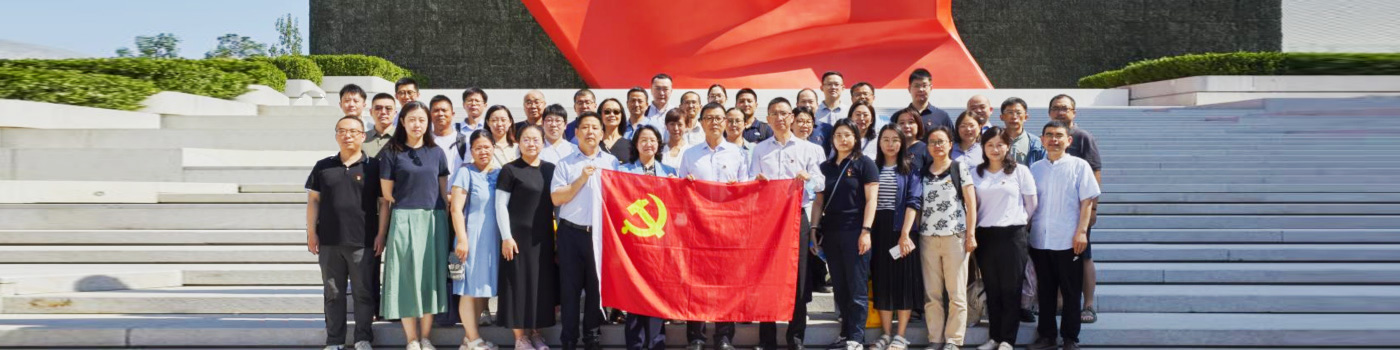
作者简介:郑筱筠(1969-),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文化研究;赵伯乐(1952-),男,江苏常熟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文化研究;牛军(1964-),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宗教哲学研究。
Buddhism and the Dragon Culture of the Bai People
ZHENG Xiao-yun, ZHAO Bo-le, NIU Ju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PRC)
Abstract: The customs of dragon worship of the Bai people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Yunnan, dragon culture of the Bai peopl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wo parts: dragon god worship and dragon B
enzu worship. The Buddhist dragon culture, fit to the primitive idea of water god in the core of the Bai's dragon culture, was not
only accepted by the Bai people but exerted certain influences on the Bai's dragon god worship and dragon Benzu worship. In t
his sense, the Bai's dragon culture became more systematic.
Key words: Bai ethnic group; Buddhism; dragon god; dragon Benzu; influence
一
在高度发达的白族文化体系中,白族龙文化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始终贯穿白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它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接受和目睹着白族文化的形成和完善。在它身上体现着白族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
就白族龙文化现象而言,其组成因素中既有反映白族先民原始宗教意识的原生型龙文化,又有源于本民族土壤却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次生型龙文化,而且还有本来产生于异质文化体系却为白族文化融摄、改造的复合型龙文化。在白族龙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汉族的龙文化、印度、藏传、大乘显密二宗的龙文化等外来文化对其完善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就其形成过程而言,远古时期的诸夏部族龙文化及三国时期汉民族龙文化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结果基本上导致了白族龙文化的原生型诞生,而初唐后,印度密教、汉传显密二宗及藏传佛教对其的影响,便是形成了次生态型和复合型龙文化,其中尤以佛教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至为关键且巨大。
白族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白族先民氐羌族群就已存在拜龙习俗,加之受到诸夏族群的龙文化的影响,渐形成较强的拜龙意识和崇龙思想。白族中存在的纹身习俗即为拜龙思想的历史见证。据调查,直至近代,大理白族中的段、王、张、杨、李、赵、何等姓氏均有纹身习俗。剑川、兰坪、云龙的白族无论男女都喜穿羊皮衣,羊尾巴保留得完好无损。①白族纹身历史悠久,史籍多有记载,《南诏野史》中,《南诏历代条》云:“哀牢山下,有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弟兄娶之,立为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皆刻画其身,象龙文,于衣后著尾。”此十姓皆为洱海区域白蛮大姓。②另据杨正权先生分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记“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的“种人”不惟指哀牢夷,亦指僰人。③此僰人即为白族先民的来源之一。自称九隆之后,并纹身以避龙虫之害或求龙蛇庇护,可从广泛流行于云南的《九隆神话》故事内涵窥见一斑。《九隆神话》实质上是感生(贞洁受孕)型民族起源神话与民族始祖神话的融合,并已熏染上了王权色彩,积淀着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④我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均详细记载九隆神话故事,另外,该书还记录了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南中,为夷制图谱事,诸葛亮所作图谱着重强调了龙与夷之始祖关系,这既是对《九隆神话》故事历史积淀层和族源起源的肯定,又反映出汉文化中龙作为灵物崇拜阶段的神龙意识向少数民族龙文化开始有意识地渗透。仔细分析《九隆神话》内容,可看出九隆神话产生的最初阶段,乃是原始的感生神话。而事实上,正是由于水的联结作用,感生型民族起源故事才得以与龙神话相溶。可以说,从《九隆神话》开始,逐渐演变、产生的各种龙文化中,其最原初、最深层的历史积淀层内涵正是崇水意识。正是由于崇水意识的深层积淀,白族龙文化才得以生存、发展。
如果说流行于大理地区的《九隆神话》尚属于未受到佛教影响的早期龙文化现象的话,那同属于这一时期的流行于鹤庆地区的龙与人类始祖的创世神话则更直接地强调了龙的始祖性特点及水的至高无上性意识。在鹤庆地区流行的《劳谷与劳泰》⑤就是这样一则关于龙的神话故事:远古时期,世上没有人类和万物。天地连在一起,中间夹着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滚烫的海水把天冲开一个大洞。天洞里冒出一大一小两个太阳,两个太阳在天上越撞越猛,小太阳被撞落到大海,大海掀起巨浪,把天穹高高顶起,将地往下冲凹,于是土地就此分开。“小太阳落进大海后,把海水煮沸了,惊醒了深睡的大金龙。大金龙一口将火红的太阳吞进了肚里,太阳在金龙的腹中猛烧,龙受不了,一甩头,撞到螺峰山上,使在喉咙中的太阳变成了一个大肉团,从龙腮中迸出炸开。炸开的肉团,又裂变成无数肉片、肉丝、肉粉到处乱飞,飞到天上的变成了云朵;悬在空中的变成了鸟雀;落在山岭上的变成了树木花草;落在山箐的变成了走兽飞禽。那撞不碎的肉核核,落地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叫‘劳泰’,第一个出现的男人叫‘劳谷’。⑥从此,世上有了人类和万物。劳泰和劳谷结成了夫妻”在这则传说中,大金龙可以作为创世主存在,其地位远远高于人类创世祖劳泰和劳谷夫妻。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金龙与水、大金龙与人类的关系显然已作为集体无意识原型沉淀于早期白族龙文化现象中。
强调龙与水的关系贯穿着白族龙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究其原因盖龙神之形成与水的关系密不可分。早在渔猎时代,人们天天与水打交道,逐渐意识到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基于对自然界的原始整合意识,人们产生了崇水意识,并进而将之具象化为生活于水中的各种动物。后来随着氏族部落集团的不断兼并,龙神作为混合了各氏族部落图腾的最高神出现,为进一步起到凝聚作用,保证各部落风调雨顺、生活安泰,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便是司水,主降雨。水作为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因素成为龙神崇拜的最深层次而又最为核心的历史积淀层,并伴随着龙神经历了原始宗教的各个形态以及人为宗教的各个发展阶段,始终不曾动摇和变异。这也是它后来能为各不同部落、各不同族群、各不同历史时段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白族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言,龙神的司水意识正是白族龙文化的核心,也是其接受诸夏龙文化、汉族龙文化、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影响的重要契机和出发点。
早在初唐时期佛教传入大理之前,洱海区域分布着众多部族,其中尤以被称为“白蛮”和“乌蛮”的两大部落群体为主。这两大部落群体是由创造了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土著族群“昆明之属”分化出来的。⑦他们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基本统一洱海区域时,构成了南诏的主体居民,亦即大理白族的主要族源。“乌蛮”和“白蛮”作为是出自“昆明之属”的同一部落群体的两大族群,他们都继承了“昆明之属”的原始宗教信仰。查诸史籍,昆明人从汉代开始就信仰巫教,巫师成为其与神沟通的神圣媒介。据《华阳国志
·南中志》记载:“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菅常以盟诅。”初唐时期,洱海区域广泛流行巫教信仰。在巫教信仰过程中,白族先民的拜龙意识并未减弱,仍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发展。及至初唐开始,佛教经由不同路线、途径和方式开始传播于洱海区域。但佛教的传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佛教受到了来自原始巫教的强大势力的顽强抵制,直到南诏中期的劝丰祐时代(公元824年~859年),佛教才经过演变和发展,逐渐成为南诏主体居民白蛮与王室的共同信仰。在佛教艰难的传布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佛典文学故事也随之传入。其中同时存在于印度佛教密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体系中的龙王龙女故事亦随之传布于白族地区。其中龙司水、主降雨、有神通、善变化,甚至能变形为人,或常具人格化,思维及行动,有眷属家族,有精美别致的龙宫,拥有奇珍异宝,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等观念,都直接由印度密教、或间接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传入。⑧尽管佛教在白族地区的传布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很多地区巫教势力根深蒂固,甚至有些地区还存在巫佛两教并存的情况,但佛典故事中文学性和趣味性较强的龙王龙女故事却迅速为广大白族民众接受,并开始影响和改造着白族原有的龙文化系统。甚至有些巫教系统的龙文化现象也局部地接受了佛教龙文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本主崇拜作为佛教与原始巫教共同斗争的最终产物而出现时,它也在白族先民原始水神崇拜的核心意识层面及王权与神权象征的文化层面上接受和继承了历史传承下来的龙文化,并以具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接受、容纳和改造了佛教龙文化。由此,白族固有的龙文化受到佛教龙文化的冲击后分裂为两个独立存在却又相互关联的龙文化群:未成为本主崇拜组成部分的龙崇拜文化群和成为本主崇拜重要组成部分的龙王崇拜文化群。亦即龙神崇拜群和龙本主崇拜群。这两大龙崇拜群同时作为白族龙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于白族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却又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且未能最终融合在一起。
二
作为非本主崇拜成员的龙神崇拜在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继续发展本民族固有的龙文化,同时也积极融摄、兼容着佛教龙文化的熏染。由于白族固有的龙文化(包括原生态型的龙文化和属于巫教内容的龙崇拜)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佛教龙文化难以成为主导,但却开始为白族固有龙文化容纳。这一龙神崇拜的悖论性特征表现为它的内容较为驳杂,有对固有的龙文化的改造,也有反映佛教(尤其是印度密教)与巫教的斗争,有的则直接表现为吸收佛教龙文化意识后,以本土龙文化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在情节设置上则表现为挪用佛典龙王龙女故事的部分情节或直接设置佛教龙文化物象于白族龙文化中。
首先,要强调的是白族龙文化始终是以原始的水神观念为核心意识发展嬗变的。如:围绕着治水这一题材,演变出斗龙型故事,如《小黄龙和大黑龙》故事中小黄龙与大黑龙之斗争,反映了白族先民企图依赖与人为善的水神小黄龙制服与人为难的水神(大黑龙)的社会意识。及至佛教文化输入,佛典中生动有趣的龙王龙女故事广泛渗入到斗龙型故事中并演变为两类:一类故事是以佛教人物或崇佛人物为主角,以其制服龙(或水患)的行为来组织故事情节的。如《师摩矣锁龙》、《杨都师驯黑龙》、《罗荃寺僧降龙》、《矣伽陀开辟鹤庆》等。其中《师摩矣锁龙》事记载于《南诏野史》:“(师摩矣)尝随祐至罗浮山白城,建一寺,南壁画一龙,是夜龙动,几损寺。妃乃画一柱锁之,始定。”⑨师摩矣是南诏王劝丰祐的宠妃,笃信佛教。这一史事记载寥寥数语已折射出佛教与巫教之间的斗争,龙则成为巫佛斗争的具象化对象,因为,巫教沿袭了白族固有的龙文化,同时,龙也存在于佛教体系中,不同的是,巫教中的龙代表了巫教势力,而佛教中的龙却是皈依佛法的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神。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以师摩矣为代表的佛教一方最后取胜。
在这几则故事中,佛教的影响较显著,而属于斗龙型故事的另一类故事,直接以自然界生物为描述对象,如《金鸡与黑龙》故事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则显得较隐晦了。这个神话主要流传于沘江流域的兰坪县和剑川县。在云龙白族中,还流传着以此传说创作的民间诗歌《金鸡传》。鸡是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勒墨人的氏族图腾。云龙县的白族有很多属于那马和勒墨支系,这一神话传说的原生态故事的核心意识应为反映金鸡氏族部落和崇龙氏族部落之间的斗争,现仍流行于兰坪县白族支系那马人之中的《金鸡与小龙的故事》⑩应属此原生态故事。佛教传入后,此故事以金鸡、龙形象为原型,对之加以改造,甚至将之纳入到佛教系统,使之分别与佛教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神金翅鸟形象与龙形象重合,这样便使原形成于大理本土文化中的金鸡黑龙故事,竟按佛教观念演变为印度佛教中金翅鸟与龙之间的战斗故事。这段斗法故事与佛典文学有较深因缘。它固与《贤愚经》卷十所述须达起精舍过程中舍利弗与牢度差斗法情节有相似之处,但佛典中见于《佛本行经》、《贤愚经》、
《生经》、《法苑珠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佛说海龙王经》、《佛说长阿含经》等等典籍关于佛世尊降服恶龙的故事以及龙与金翅鸟争斗的故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在印度神话传说中,龙与金翅鸟为天敌,并由此敷演出较多动人故事。后来被佛教徒加以吸收、改造后成为佛典文学中较生动有趣的精彩物语,龙与金翅鸟也相应成为佛教护法神。(11)据《佛说长阿含经》卷四《分世记经·龙鸟品》所记的一段文字可对龙与金翅鸟的斗争略窥一斑:
卵生金翅鸟欲搏食龙时,从究罗睒摩罗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湿生化生诸龙。若胎生金翅鸟欲搏食卵生龙时,从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若胎生金翅鸟欲搏食胎生龙时,从树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湿生化生诸龙食也。湿生金翅鸟欲食卵生龙时,从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若湿生金翅鸟欲食湿生龙时,从树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八百由旬,取湿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化生龙食之。若化生金翅鸟欲食化生龙时,从树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12)
在这段优美的佛典物语中,龙始终是处于劣势,为金翅鸟固定取食的对象,尽管在后来的佛典记载中,金翅鸟与龙因皈依佛法,成为佛教护法神,它们之间的关系稍有所改善,但金翅鸟能战胜龙这一观念却根深蒂固地被沿袭下来,并随佛教的传播而四处流布,迄今为止,许多佛塔建筑上仍铸有金翅鸟的形象以厌龙。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尤为明显,不仅在民间传说中多有金鸡(亦即金翅鸟)与龙争斗的故事,而且在日常生活习俗建筑雕塑中也多有反映。
佛教对白族龙神崇拜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对斗龙型故事的影响,它也表现在故事情节、故事主人公形象的设置方面。这一类较著名的莫过于《玉白菜》、《牧童和龙女》类故事。
《玉白菜》的传说“在大理、洱源一带流传较广,异说、异文也较多。建国以来曾经李中迪、杨玉春、王寿春、杨宪典等同志搜集记录过。其中杨玉春和王寿春同志搜集记录的《九龙守护玉白菜》主要人物和情节都与此文略有出入。其它异文都大体相同。”(13)《玉白菜》的故事异文较多,但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吸收和接受了佛教龙文化中龙王、龙宫观念和龙宫藏有珍宝的观念。
《牧童和龙女》类故事流行于剑川、鹤庆,另有流行于鹤庆地区的《牧笛吹动龙女心》故事异文,后者较前者的故事记载更为完善和动人。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但融摄了佛教龙文化中的龙王、龙宫观念,而且塑造了美丽善良而又纯情可爱的龙女形象,并围绕着龙女与人间小伙的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为核心来敷演、设置故事内容。《笛声吹动龙女心》故事是这样的:龙王的独生女小玉因喜爱人间传来的笛声而不顾龙宫禁令,在鲤鱼婆婆的陪伴下找到了吹笛子的人间牧羊小伙阿虹,心生爱慕。后来便常离开龙宫来人间听阿虹吹笛子,这事为龙王所知,龙王大怒,后经龙女的伯父大黑龙劝说,终于使有情人终成眷属。(14)这一故事受佛教影响较显著。龙王、龙女、龙宫的设置固受印度佛教龙文化观念的熏染,而其故事情节的营造受汉唐传奇《柳毅传书》的影响较显著。洞庭龙女因牧羊而与书生柳毅相遇,并演绎出一则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事实上,汉文化的这则《柳毅传书》故事正是佛教龙文化影响的集大成者。它一经形成便迅速流布开来,势必也会随着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影响而进入到白族地区,并为白族人民所喜爱。
三
如果说龙神崇拜对佛教龙文化的接受还处于初步、保守的阶段的话,那么白族本主崇拜中的龙王崇拜则是以开放性的博大胸怀容纳、接受了佛教龙文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白族固有的龙文化继续吸取佛教龙文化输送的营养成份,改造和完善白族龙文化,并进而形成白族的龙本主崇拜,二是白族文化以全开放的心态将印度密教中的八大龙王及大黑天神、观音、诃利帝母等佛典人物完全纳入本民族体系,使之成为本民族的本主而加以顶礼膜拜。
白族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民族宗教,它的形成与发展,与佛教的传入及其本土化的过程关系甚密。据史籍记载,白族最早出现的本主神是密宗的护法大黑天神,而最早出现的本主庙是供奉大黑天神的大灵庙,(15)这足以说明本主神像、神庙的出现,与佛教,尤其与印度密宗有直接关系。由于白族本主崇拜是一种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以村社和水系为纽带的民族宗教,故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本主崇拜的核心就是祈雨水、求生殖、祷丰收。本主作为村社的保护神,它与农耕生产密切相关,尤其与白族的稻作文化关系紧密,龙神作为本主被崇拜,其首要功能就是司水、主管降雨,这与白族固有龙文化的核心意识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它融摄、改造外来的佛教龙文化的前提。例如:段赤诚为民除害而葬身蟒腹的故事在大理家喻户晓,在史籍《南诏野史》、《白古通记》中都有记载。这一故事应是现实社会中白族人民征服自然灾害的真实反映,段赤诚却因此而被奉为龙王,并且尊为本主,在大理很多地区都有他的本主庙。段赤诚以一位民间英雄的身份被奉为龙本主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白族龙文化中原始的水神观念的作用。当佛教龙文化传入后,段赤诚除蟒故事在原有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补充,它吸取了佛教龙文化中龙王与眷属的家庭观念,合情合理地为段赤诚这位洱河龙王增加了一位妻子,建立了龙宫,使段赤诚龙王崇拜更富于温馨的家庭观,充满了人情味。如:在“洱源海潮河村‘四生慈父大黑天神’,庙中现存木雕像10尊,每尊高约米余。按神台的从右到左的顺序来看,第一堂祀神是‘龙王’段赤诚,着古代官服,戴南诏、大理国似的头囊,蓄八字胡,脚踩一条昂首的盘蛇,其右侧为披蛇鳞衣的妻子。”(16)
为龙本主配以妻子儿女、组建家庭、构筑充满温馨和亲情的龙宫,是白族龙本主崇拜受佛教龙文化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
佛经故事中的龙王婚配观念是古印度人类社会婚姻观念的反映。正如人类社会一夫多妻制一样,佛典中的龙王可以拥有无数美妾妻子,例如《佛说海龙王经·授记品第九》记载:
于是海龙王白佛言,我从初劫止住大海,从拘楼秦如来兴于世来,大.海之中诸龙妻子眷属甚少,今海龙众妻子眷属繁裔甚多,设欲计较不可穷尽……(17)
从海龙王禀告佛世尊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佛典所叙述的龙王家族是庞大的,“众妻子眷属繁裔甚多”,大有人间皇族贵胄热热闹闹、兴旺发达的气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佛典中龙王拥有无数眷属妻子的观念传到大理白族地区后,它对白族龙本主家族的形成、家庭的建立起到了启悟作用,但这庞大的妻妾观念却并未被白族人民接受。白族龙本主的家庭仍属于一夫一妻制,儿女的数量也较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运用夸张手法。事实上,受到佛教眷属观念启发后产生的白族龙本主家庭观念已含有人间社会血缘关系的成分。例如:洱源地区境内多湖泊、河流,其中被封为邓川至江尾一带的本主神都是具有血亲性质的一个大家庭成员。它以浪穹龙王段老三为家庭的长者,其长子王懿白子景帝被永华乡各村尊为本主,二子僰子景帝是乔后玉清河本主,三子白子爱民景帝为芘碧大庄水系本主,四子黄龙景帝是大小果水系本主,五子罗浮景帝乃是茨菜哨平水系本主,六子护国佑民皇帝是横水河系本主,七子清子景帝为力头等村本主,八子护国佑民景帝是海口等村本主,九子九神神王是汉登等村本主,长女龙姑奶奶是祥云云南驿龙王,二女白王姑老太是力头村一带龙女,三女龙姑老太是漏邑等村龙王娘娘。(18)浪穹龙王段老三这一庞大的九子三女家庭显然是根据现实生活中各水系之关系建立起来的。原来各自分散的支流与主干的各水系之关系在这一龙本主家庭中被具象化,却更显出人情特征。现广泛流传于大理地区的《河头龙王的家系》就是对这一庞大的龙本主家庭的文学性描述。
另外,《洱海祠》、《本主的女儿》、《三娘娘》等本主故事显然都属于这类吸取了佛典龙文化的观念或故事情节加以改造形成的。
白族龙本主崇拜的另一特点是:将印度佛教神系中的龙王纳入到本民族宗教中。
在印度佛教体系中,龙王及其诸多眷属数不胜数,不可计量。但在这无数的龙王及其眷属中,有八大龙王:难陀龙王、跋那陀龙王、和修吉龙王、娑遏罗龙王、德叉伽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婆罗龙王。这八大龙王神通广大,在龙部中最为著名。它们的形象在著名的南诏画卷《张胜温画卷》中均有所表现。然而在龙本主崇拜中被列为本主的主要是跋难陀龙王和和修吉龙王。和修吉隆王,梵名Vasuki,意译为宝有龙王、宝称龙王、多头龙王,又称婆修竖龙王、筏苏积龙王,白族地区称之为婆娑吉龙王,当为和修吉音异译。在印度传说中,能绕妙高山,并以小龙为食。它也被白族人民奉为本主。然而最有名的印度龙王本主化的应是跋难陀龙王。白族人民将之称为白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梵名Vpannda,又作婆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意译为重喜龙王、延喜龙王、大喜龙王、贤喜龙王。它与难陀龙王是兄弟,亦因善调御风雨,善能顺应人心,深得百姓喜爱,固有大喜等名称。据《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所载,昔时佛陀至三十三天为母说法时,难陀、跋难陀龙王见彼诸沙门飞行于天上,遂兴起嗔心,欲大放火风阻止,后为目犍连所收伏,乃随众至佛所,听佛说法,并皈依佛门,成为佛教护法神。另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载,佛陀诞生时,难陀和跋难陀龙王二兄弟于虚空吐清净水,一温一凉,以灌太子之身。在密教中,跋难陀龙王位于胎藏界外金刚部院中之南、西、北三门之左边。(19)在白族本主崇王中的白难陀龙王深受白族人民的尊敬和喜爱,在《张胜温画卷》第十二图有其佛像:人形,膝下垫蛇,头上有数个蛇头向前伸出,其左右有护卫神六尊拱卫,其座下有鸡头人身、狗头人身各一供养。今大理下关北郊宝林寺本主庙祀段赤诚和白难陀龙王为本主,是苍山上一处比较重要的本主神。(20)另外,剑川县金华镇北门、甸南回龙等村亦祀白那陀龙王为本主。白难陀龙王作为异质文明的产物能为白族人民原封不动地加以吸收,并作为重要的本主神加以供奉,已属不易,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它竟能与历史源远流长的段赤诚龙王平分秋色,共同分享同一庙祀香火。究其原因,盖与其在印度传说中善调御风雨、能顺应民心,因有
大喜等名称这一因缘有关。成为白族龙本主后,它亦能以其善调御风雨的形象满足白族人民对本主神祗的功利性崇拜目的,同时又与白族固有龙文化要求体现的最原始的历史核心意识水神观念相契合,故而它为白族人民喜爱也属必然。
综上所述,佛教对白族龙文化体系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通过分析,我们可发现佛教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有两条规律:其一,佛教首先融合于白族传统巫教后,再渗入和影响白族龙文化;其二,佛教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始终是围绕司水职能为核心层面来进行的。
注释:
① 田怀清:《白族纹身趣谈》,载《民族文化》(云南)1986年第5期。
②③ 杨正权:《龙与西南古代氐羌系统民族》,载《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
④ 参见张福三主编《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赵橹《九隆神话探源》,见《云南少数民族论集》,第1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1982年版。黄惠焜、傅光宇等先生的论著中均涉及此。
⑤ 《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⑥ 劳泰,白语,意为始祖母;劳谷,白语,意为始祖父。
⑦ 尹明举、李东红:《略论白族的形成》,载《白族学研究》第2辑。
⑧ 印度Naga,梵语意为“蛇”,在汉译佛典中被转译为“龙”。印度密教中的Naga崇拜传布到大理后,出于同样原因,亦被转译为“龙”。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⑨ 《南诏野史》胡蔚本。
⑩ 见《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11) 有的学者认为,《金鸡与黑龙的故事》源于佛典文学《牢度差斗圣》故事。笔者以为,《牢度差斗圣》故事有可能会对之影响,但佛典文学中龙王龙女故事与之有更深因缘。
(12) 《佛藏要集选刊》第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另:在印度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龙与金翅鸟分别有卵生、湿生、胎生、化生四类。这是印度古代人民唯灵论观点的反映。
(13)(14) 参见《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书中姜祥先生写的附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第125页。
(15) 李东红:《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16) 参见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7) 《大正大藏经》卷15。
(18) 参见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9) 参见弘学著《佛教图像说》,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74页。另见《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所行讚》、《佛说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法苑珠林》等佛典多有论及。
(20) 参见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1)02-0054-05
收稿日期:2001-01-03
基金项目: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云南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之子课题“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1.来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