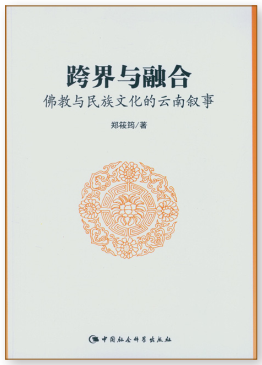
郑筱筠著作《跨界与融合——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以下简称《跨界与融合》),从大文化的概念出发,对云南民族文学及其宗教因素做出内生性关系特点研究,在宏观写作上不受具体的历史时间顺序限制,以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个案解读构成专题性的综合研究,从而对佛教与民族文化以不同方式参与建构云南民族文化体系做出有效探究。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的建构
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所表现出的民族多样性特征也最为突出,这一点也反映在云南文学上。《跨界与融合》一书中,郑筱筠以龙图腾的文本呈现作为切入点,来彰显云南文学的特殊性。针对相同的母题与描摹物,云南文学无疑更富于民族文化色彩的意象和象征。龙普遍存在于中华文明中,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图腾,其文化内涵始终贯穿于云南各民族发展过程。而且,“龙”这一形象隶属于汉语符号体系,也归属于汉语文化体系,同时也被云南各族广泛接受。《跨界与融合》一书中细述云南文学的特殊性,不仅受族群文化因素、族别文化成分以及村寨文化影响,中原文化、南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也对云南文学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龙”叙事横向串联起云南各民族文学的同时,书中也进行了纵向剖析,比较其影响异同。如傣族男子历史上沿袭的纹身,多在腰部或四肢,纹龙、狮、虎、象等凶猛动物,源于远古时期先民对蛟龙的惧怕躲避而衍生出的崇龙习俗。在诸多创世传说中,龙是许多民族的创世祖先,与各族群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如《召怯龙慕钪》传说所言,人身龙尾的圣物召怯龙用尾巴将先民悉数卷入布朗洞里,只剩下兄妹二人,他们彼此通婚,才孕育出傣族;白族神话《劳谷与劳泰》里塑造出先于“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劳谷与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劳泰”而存于世间的大金龙,其地位远远高于人类创始祖劳谷、劳泰夫妇;东巴经典《美生都丁哲作》中,通篇围绕着人(美生都丁)与龙(古鲁古究)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展开叙事,并以此构建故事情节。龙王古鲁古究是自然神的象征,因此,人对龙的触犯是对大自然的触犯,展现出纳西族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禁忌。
《跨界与融合》一书正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相同母题下,不同民族文学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表现出差异性特征,作者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用较多篇章勾勒描摹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版图,记录以神话、传说、唱诗等形式出现的民族文学,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地位也得以直接呈现。
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云南具有多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传统的文学史写作中,多借助文学文本的形式层面,而忽略重要的田野调查,或者说,与大多数文学评论者而言,实地调研一事遥远而陌生。而郑筱筠在《跨界与融合》一书的写作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田野调研,记录当地的文学、习俗与信仰,并以录音、录像、图片等形式保存,积累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种以文学人类学视域为中心的新范式适用于文学研究,以云南文学中的观音形象为例,众所周知,《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优美的语言对观音的精神、美德等做了文学性表述,后世文学多以此为主题对观音的显圣事迹加以敷演。纵观以观音为主人公衍生的各类民间传说,男身造型与女身造型的观音形象共存于云南民间文学中。这两种造型属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交叉并存于同一时空,体现出兼容性的民族文学特征。通过田野调研,其形象特征及演变已不在只是文本分析,而是通过祭祀、碑刻、文物、图像等在野外调查到的成果,厘清观音信仰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发展轨迹与规律,具有学术前瞻性。
《跨界与融合》一书中的田野调研所带来的不只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补充,其本身更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带给我们方法论的反思。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与“民间”之间,作者更倾向于重视大传统及民间的材料,而非传统所强调、重视的正史文本,采用材料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地方志、民族志、山志、寺观志、小说、民间传说、故事、笔记、艺术作品等,皆可以采用。也正因此,研究更加深化而细化,在全球化浪潮的来临下,以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审视云南民族文学,更促成民族文化自觉,本土化的地域特色也得以彰显。
三、 经典文本钩沉
对民族文学中最著名的经典做个案解读,从具体文本出发以推陈文学内涵、传播范式与理路,历来被看成是最能彰显作者文献功底、逻辑能力的传统方式。在《跨界与融合》一书中,作者摄取少数民族地区最著名的传说文本,对之进行丰富而翔实的考证和讨论。通过钩沉傣族地区妇孺皆知的《召树屯》故事,以探究云南文学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原文化因子之选择与汇融过程。
《召树屯》故事题材源于印度说为作者所认同,同时,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疏理,在诸多印度梵文本佛经或佛经故事中找到大量与《召树屯》题材相近的文本。毫无疑问,《召树屯》故事的生成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它自出现在云南的傣族地区开始,一直围绕着原生态的召树屯故事进行复合改编,以至于逐渐形成故事主要情节脉络相同,但在具体细节上有差异的许多亚故事型并存于同一地区的文学现象。
诚然,在云南地区,此类民族文学保存的媒介各异,通常巴利语佛典是此类故事存活的原始载体,再通过民间口耳相授、口头流传的文学形式进行传播,因此,傣族民间歌手(或为故事讲述者)“赞哈”们保存着歌唱用的手抄本,故事文本或以诗歌形式或以传说形式呈现,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被整理成书。
这一类民族文学从东南亚佛教地区传入,随着宣导,其中文学性、趣味性较强的佛典故事逐渐为人们熟知,继而成为接受度较高的口传文学故事。此类故事有大众性、通俗性、传承性及变异性特征,在流传的过程中,叙述者为适应受众的需要,往往要作适当的调整与删减,以期符合口头传授文学,因此通常以韵文形式出现。
研究云南民族文学的著作并不算少,然而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民族文学依旧面目模糊,不为人所知。各种原因共存,造成了这种局面:文学的发生地及创作主体处于中国版图的边缘,与传统的中原文学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以部分故事并不符合中原受众的阅读心理。地理与文化的双重边缘性使云南民族文学少为人知,郑筱筠面对云南多样的民族及地域特色,借助文学文本的形式层面,挖掘出文本最深处的文化内涵。同时,又通过宗教学理论的参与,加深了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并从中寻觅出具体的隐喻及价值所在。
在今天看来,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语境下,云南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郑筱筠不仅以历时性眼光,且以共时性态度将云南文学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进行研究分析,着力理清云南文学的内敛与外显。《跨界与融合》一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云南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补充,且有助力云南民族融合、宗教和顺的现实意义,是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研究由边缘到中心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司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古代文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
(来源:《中国宗教》2019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